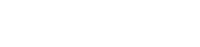接著,他声音陡然转沉,带著不容置疑,
“此事,绝无任何转圜可能。孙儿心意已决,望祖母明察。”
“孙儿告退。”
说完,他不再多言,再次一揖。
转身的剎那,他的目光轻轻掠过了坐在一旁的大夫人孟氏。
仅此一瞥。
隨即,他便收回所有视线,迈开沉稳的步伐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正厅。
孟氏觉察到江凌川的冷瞥,心中一凛,但隨即又轻哼出声。
江凌川离开后,厅內只剩婆媳二人。
老夫人疲惫地靠向身后的锦垫,手中那串沉香木佛珠捻动的速度缓慢而沉重。
孟氏没有立刻起身,仍安静坐在下首,垂眸思量著什么。
她回想起了方才。
杨四小姐那句“二爷心里有旁人”,说得淒楚,却字字分明。
那分明是意有所指。
这“旁人”……
她眼前驀地闪过“文玉”那张低眉顺目的脸。
是了。
前几个月文玉下落不明时,那煞星是何等情状?
连晚吟一句玩笑,都惹得他当场拔刀。
若只是寻常逃奴,何至於此?
若真是文玉……
一个丫鬟,先是惹得兄妹反目,如今更是搅得未来夫妇反目成仇。
这样的祸水,怎配留在府中?
片刻后,孟氏抬起眼,目光已是一片沉静的清明。
她望向主位的老夫人,缓缓开口:
“母亲,有句话……儿媳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见老夫人微微頷首,孟氏声音放得轻柔,带著恰到好处的疑惑:
“母亲,二郎方才虽否认得坚决,可杨四小姐那话……不知那『旁人』,是否真有所指?”
老夫人闻言,没有立刻回答。
她望著孙子方才站立的地方,仿佛还能看见他决绝挺直的脊背。
“哎……孟氏啊,”
老夫人摩挲著温润的佛珠,声音有些飘忽,
“你嫁进来这些年,二郎的性子,你也是看在眼里的。”
“他若是真把什么人……放在了心尖上,当成了自己人。”
“依照他那莽直冷倔、偏执执拗的性子,他怎会將人送到我这儿,改名换姓,不闻不问?”
孟氏闻言,若有所思,微微頷首。
老夫人这番话,確实在理。
以江凌川那说一不二、占有欲极强的性格。
若真对那文玉有特殊情分,岂会容她离开寒梧苑,安置在老夫人这里?
这確实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。
“母亲说的是,是儿媳多虑了。”
孟氏垂下眼帘,温顺地应道,脸上恢復了平日的端庄持重。
孟氏面上虽是如此说,可心底那点疑虑,终究是像种子般悄然埋下。
老夫人揉了揉额角,面露倦色。
孟氏见状,不再多言,恭敬告退。
待她离去,老夫人才由采蓝扶著,缓缓走向小花园。
原本热闹的正厅,骤然空寂下来。
无人在意的西侧茶房里,更是静得落针可闻。
只有红泥炉上那把光亮的银銚子,里面的水將沸未沸,持续发出细微的嘶嘶声。
唐玉僵立在茶案旁,仿佛一尊失了魂的泥塑。
自从杨令薇那句“二爷心里有旁人”、“令薇愿自贬为妾”的话石破天惊般砸出来。
她的心就一直高高悬在嗓子眼。
像是被一根无形的丝线吊著,悬在万丈深渊之上。
耳边是呼啸的冷风,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。
仿佛下一步踏空,便会粉身碎骨,万劫不復。
她甚至忘了呼吸,忘了动作。
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那一帘之隔的正厅,捕捉著每一句对话,每一个语气。
直到此刻,正厅內人声散去,寂静蔓延。
直到身旁负责递送茶水的小丫鬟小月,有些疑惑地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唐玉这才如梦初醒般,回过神来。
她这才感觉到,自己一直死死攥著胸前衣襟布料的手。
指节因为过度用力,已经绷得惨白,微微颤抖著。
她的心神虽因这场谈判的结束而稍松。
可方才正厅里那番唇枪舌剑、字字诛心的交锋,却在她脑海中疯狂翻涌、衝撞,不肯停歇。
一时是杨令薇那张泪流满面、却字字淬毒的脸。
淒楚哀婉地说著“愿与那位姑娘,姐妹相称,平起平坐,绝不敢有半分爭抢之心”;
一时又是江凌川那张冰冷含煞的侧脸。
他毫不留情的冷笑,斩钉截铁的说著“寧娶布衣贤女,不纳中山之狼”、“绝无转圜”。
接著又是大夫人所说的“不知那『旁人』,是否真有所指?”
这几句话,反覆在她脑中迴响。
將她的心绪时而拋上令人窒息的云端,时而又狠狠摁入冰冷的寒潭。
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峰迴路转,惊心动魄。
让她直到此刻仍觉心口狂跳,四肢发软。
老夫人最后所说的,算是给她下了一个定论。
即她不可能是二爷的心上人。
她不是江凌川的心上人。
自然的,也不会是那祸乱家宅的祸水,也没有被根除的必要。
事到如今,她只有反覆咀嚼老夫人的这两句话,才能从中汲取一点点微薄的安全感。
没想到江凌川如今刻意的疏离和冷漠,竟成了她最后保命符。
思及此,她心绪有些复杂。
她想起江凌川的话。
“我江凌川,何时与你透露过半句,我有什么所谓的『心上人』?!”
“你这般言之凿凿,是在替我认下什么风流债,还是在凭空污我清誉,臆测我內帷不修,私德有亏?!”
他这话,是当著老夫人和大夫人的面。
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否认了“心上人”的存在。
將杨令薇的指控定性为凭空污衊、臆测抹黑。
他撇清了自己,也等於间接將她从这场风暴的中心,摘了出来。
想到这,唐玉紧紧攥著的五指,终於稍稍鬆开了些。
掌心被指甲掐出的月牙形红痕清晰可见。
一股微弱的庆幸涌上心头。
不知是真心还是偶然,在那种情境下,他竟还有心护著她。
她闭了闭眼,在心底轻声道了句:谢谢。
心神微松,她呼出一口滯闷在胸口的浊气,又想起眼前。
眼下最要紧的是,江凌川与杨令薇的婚事。
他们俩的婚事一日没有彻底了断,尘埃落定,她便一日不得真正的安生。
今日杨令薇虽然自曝其短,看似劣跡斑斑。
但退婚这等大事,牵扯两家顏面,甚至可能涉及朝堂关联。
最终拍板的,是建安侯爷,是杨家的当家老爷。
老夫人虽然发了话,表了態,但侯爷……会同意吗?
“此事,绝无任何转圜可能。孙儿心意已决,望祖母明察。”
“孙儿告退。”
说完,他不再多言,再次一揖。
转身的剎那,他的目光轻轻掠过了坐在一旁的大夫人孟氏。
仅此一瞥。
隨即,他便收回所有视线,迈开沉稳的步伐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正厅。
孟氏觉察到江凌川的冷瞥,心中一凛,但隨即又轻哼出声。
江凌川离开后,厅內只剩婆媳二人。
老夫人疲惫地靠向身后的锦垫,手中那串沉香木佛珠捻动的速度缓慢而沉重。
孟氏没有立刻起身,仍安静坐在下首,垂眸思量著什么。
她回想起了方才。
杨四小姐那句“二爷心里有旁人”,说得淒楚,却字字分明。
那分明是意有所指。
这“旁人”……
她眼前驀地闪过“文玉”那张低眉顺目的脸。
是了。
前几个月文玉下落不明时,那煞星是何等情状?
连晚吟一句玩笑,都惹得他当场拔刀。
若只是寻常逃奴,何至於此?
若真是文玉……
一个丫鬟,先是惹得兄妹反目,如今更是搅得未来夫妇反目成仇。
这样的祸水,怎配留在府中?
片刻后,孟氏抬起眼,目光已是一片沉静的清明。
她望向主位的老夫人,缓缓开口:
“母亲,有句话……儿媳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见老夫人微微頷首,孟氏声音放得轻柔,带著恰到好处的疑惑:
“母亲,二郎方才虽否认得坚决,可杨四小姐那话……不知那『旁人』,是否真有所指?”
老夫人闻言,没有立刻回答。
她望著孙子方才站立的地方,仿佛还能看见他决绝挺直的脊背。
“哎……孟氏啊,”
老夫人摩挲著温润的佛珠,声音有些飘忽,
“你嫁进来这些年,二郎的性子,你也是看在眼里的。”
“他若是真把什么人……放在了心尖上,当成了自己人。”
“依照他那莽直冷倔、偏执执拗的性子,他怎会將人送到我这儿,改名换姓,不闻不问?”
孟氏闻言,若有所思,微微頷首。
老夫人这番话,確实在理。
以江凌川那说一不二、占有欲极强的性格。
若真对那文玉有特殊情分,岂会容她离开寒梧苑,安置在老夫人这里?
这確实不符合他一贯的行事作风。
“母亲说的是,是儿媳多虑了。”
孟氏垂下眼帘,温顺地应道,脸上恢復了平日的端庄持重。
孟氏面上虽是如此说,可心底那点疑虑,终究是像种子般悄然埋下。
老夫人揉了揉额角,面露倦色。
孟氏见状,不再多言,恭敬告退。
待她离去,老夫人才由采蓝扶著,缓缓走向小花园。
原本热闹的正厅,骤然空寂下来。
无人在意的西侧茶房里,更是静得落针可闻。
只有红泥炉上那把光亮的银銚子,里面的水將沸未沸,持续发出细微的嘶嘶声。
唐玉僵立在茶案旁,仿佛一尊失了魂的泥塑。
自从杨令薇那句“二爷心里有旁人”、“令薇愿自贬为妾”的话石破天惊般砸出来。
她的心就一直高高悬在嗓子眼。
像是被一根无形的丝线吊著,悬在万丈深渊之上。
耳边是呼啸的冷风,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。
仿佛下一步踏空,便会粉身碎骨,万劫不復。
她甚至忘了呼吸,忘了动作。
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那一帘之隔的正厅,捕捉著每一句对话,每一个语气。
直到此刻,正厅內人声散去,寂静蔓延。
直到身旁负责递送茶水的小丫鬟小月,有些疑惑地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唐玉这才如梦初醒般,回过神来。
她这才感觉到,自己一直死死攥著胸前衣襟布料的手。
指节因为过度用力,已经绷得惨白,微微颤抖著。
她的心神虽因这场谈判的结束而稍松。
可方才正厅里那番唇枪舌剑、字字诛心的交锋,却在她脑海中疯狂翻涌、衝撞,不肯停歇。
一时是杨令薇那张泪流满面、却字字淬毒的脸。
淒楚哀婉地说著“愿与那位姑娘,姐妹相称,平起平坐,绝不敢有半分爭抢之心”;
一时又是江凌川那张冰冷含煞的侧脸。
他毫不留情的冷笑,斩钉截铁的说著“寧娶布衣贤女,不纳中山之狼”、“绝无转圜”。
接著又是大夫人所说的“不知那『旁人』,是否真有所指?”
这几句话,反覆在她脑中迴响。
將她的心绪时而拋上令人窒息的云端,时而又狠狠摁入冰冷的寒潭。
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峰迴路转,惊心动魄。
让她直到此刻仍觉心口狂跳,四肢发软。
老夫人最后所说的,算是给她下了一个定论。
即她不可能是二爷的心上人。
她不是江凌川的心上人。
自然的,也不会是那祸乱家宅的祸水,也没有被根除的必要。
事到如今,她只有反覆咀嚼老夫人的这两句话,才能从中汲取一点点微薄的安全感。
没想到江凌川如今刻意的疏离和冷漠,竟成了她最后保命符。
思及此,她心绪有些复杂。
她想起江凌川的话。
“我江凌川,何时与你透露过半句,我有什么所谓的『心上人』?!”
“你这般言之凿凿,是在替我认下什么风流债,还是在凭空污我清誉,臆测我內帷不修,私德有亏?!”
他这话,是当著老夫人和大夫人的面。
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否认了“心上人”的存在。
將杨令薇的指控定性为凭空污衊、臆测抹黑。
他撇清了自己,也等於间接將她从这场风暴的中心,摘了出来。
想到这,唐玉紧紧攥著的五指,终於稍稍鬆开了些。
掌心被指甲掐出的月牙形红痕清晰可见。
一股微弱的庆幸涌上心头。
不知是真心还是偶然,在那种情境下,他竟还有心护著她。
她闭了闭眼,在心底轻声道了句:谢谢。
心神微松,她呼出一口滯闷在胸口的浊气,又想起眼前。
眼下最要紧的是,江凌川与杨令薇的婚事。
他们俩的婚事一日没有彻底了断,尘埃落定,她便一日不得真正的安生。
今日杨令薇虽然自曝其短,看似劣跡斑斑。
但退婚这等大事,牵扯两家顏面,甚至可能涉及朝堂关联。
最终拍板的,是建安侯爷,是杨家的当家老爷。
老夫人虽然发了话,表了態,但侯爷……会同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