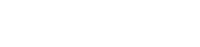他逼视著杨令薇,声音陡然拔高,带著雷霆之怒:
“你口口声声,为我那莫须有的心上人著想,处处体贴,甚至『甘愿』贬妻为妾……”
“我倒要问问你,我江凌川,何时与你透露过半句,我有什么所谓的心上人?!”
“你这般言之凿凿,是在替我认下什么风流债,还是在凭空污我清誉,臆测我內帷不修,私德有亏?”
“你既已知错,便该诚心悔过,静思己过。如何悔过,自有家法规矩裁定。”
“而不是在这里,以退为进,搬弄是非,顛倒黑白,搅得家宅不寧,让长辈烦心!”
江凌川对著老夫人和孟氏,郑重一揖到底,声音沉痛决绝:
“祖母,母亲明鑑!”
“此女,婚前便已失手伤姐,德行有亏;身边奴僕亡故事出蹊蹺,惹人非议,已损及自身与家族清誉;”
“如今,更因莫须有的妒忌,竟敢在长辈面前,妄言自贬,搅乱伦常,视婚姻礼法如无物!”
“桩桩件件,皆已证明其品行不端,心术不正!”
他抬起头,目光如炬,斩钉截铁:
“敢问祖母、母亲——”
“如此不堪之人,如何还能再为我侯府之媳?!”
杨令薇闻言,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衝上了头顶,又瞬间冻结。
她跪在地上的五指猛地收紧。
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,才勉强维持住摇摇欲坠的身体。
她猛地抬头,望向江凌川的眼神里,是再也掩饰不住的恨意与疯狂。
他怎么敢!
怎么敢在长辈面前,如此不留情面地彻底否定她!
孟氏也被江凌川这毫不留情的决绝姿態惊了一下。
下意识地看向主位的老夫人。
老夫人面色沉凝如水,眉头紧锁,手中佛珠捻动的速度不自觉地加快。
她的目光在跪在地上形容狼狈的杨令薇,与躬身作揖態度决然的孙子之间,来回逡巡。
厅內空气仿佛凝固,只余下压抑的呼吸声。
半晌,老夫人长长地嘆息了一声。
“哎……”
老夫人缓缓开口,声音带著久经世事的疲惫,但语气却坚决,她道,
“常言道,家门娶妇,德行为先。今日,无论杨四小姐所言是真是假,是实是虚。”
“你们二人之间……怨懟已深,性情难合,已是明摆著的事实了。”
她看向杨令薇,目光复杂,但其中的疏离与否定清晰可见:
“如此情形,纵使勉强成婚,也绝非佳偶天成,只怕要成一对怨偶,终日爭执,家宅不寧……”
“这绝非家族之福,亦非你二人之幸。”
老夫人顿了顿,语气更沉,一锤定音:
“此事,关乎两府顏面与子弟终身,已非老身一人可独断。”
“杨小姐,你……今日先回去罢。”
杨令薇闻言,如遭雷击,浑身剧震。
慌乱、不甘、恐惧的目光,瞬间投向了坐在老夫人下首的孟氏,眼中满是最后的祈求与暗示。
孟氏接收到了杨令薇那急切求救的眼神。
她眼睫微垂,避开了那目光,沉吟一瞬,才抬眼看向老夫人。
声音温和带著附和:
“母亲所言极是。结亲本是结两姓之好,守望相助。”
“若结亲反结成了仇,酿出怨偶,確是家门不幸。”
不过,她后面话锋一转,只道:
“只是……婚姻大事,终究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”
“此事体大,还需侯爷回府之后,与杨家老爷当面细细商议,方能最终定夺。”
说罢,孟氏这才將目光重新投向地上脸色惨白、摇摇欲坠的杨令薇,语气是带著疏离的劝诫:
“杨四小姐,今日你也听了,也说了。且先回去,平心静气,好生……反省己过。”
她特意在“反省”二字上略略加重,目光意味深长:
“若真有错,需得真心懺悔,切实改过,方是……立身之正道。”
“回去,也將老夫人的意思,细细稟明你父母吧。”
杨令薇听著大夫人那番话。
只觉得浑身力气瞬间被抽空,四肢百骸一阵酸软,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微微晃了一下,几乎瘫软在地。
完了……
她脑中一片轰鸣,事到如今,竟还是要走到退婚这一步吗?!
不,她不甘心!
她猛地抬头想爭辩。
却对上大夫人孟氏制止的眼神。
杨令薇胸口剧烈起伏,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。
最终还是在那无声的威压下,认命地闭上了嘴。
所有的怨恨、不甘、疯狂,都被强行压回心底,化作更深的毒。
她踉蹌著,几乎是被身旁的丫鬟丁香半拖半扶地架了起来。
她对著上首的老夫人和孟氏,用尽最后力气,行了一个失魂落魄的礼,声音低哑破碎:
“令薇……告退。”
厅內只剩自家人。
江凌川没走。
他就那么静静地立在原地,身姿笔挺,目光幽沉,周身散发著尚未散尽的寒意。
正厅內一时静得落针可闻,只有香炉里细烟裊裊。
老夫人看著他,眼中带著疲惫,也有一丝复杂难辨的情绪。
她捻动佛珠的手停下,缓缓开口,声音比方才更显苍老:
“二郎。”
江凌川闻声,终於有了动作。
他上前一步,对著老夫人深深一揖,姿態恭谨,脊背挺得笔直。
“祖母。”
老夫人看著他低垂的头顶,嘆了口气:
“今日……你也看到了。杨家这门亲事,怕是难了。只是……”
她顿了顿,目光带著审视,
“方才杨四丫头口中,你那『心上人』……是怎么回事?”
孟氏也抬起眼,目光落在江凌川身上,带著惯常的温和,以及一丝不宜察觉的探究。
江凌川缓缓直起身,迎上老夫人的目光,脸上一片坦然的沉静。
他开口,声音清晰,字字分明,既是回答,也是宣告:
“回祖母,孙儿並无什么『心上人』。”
他目光扫过一旁同样注视著他的孟氏,语气平淡却斩钉截铁:
“不过是杨氏为遮掩自身罪愆、搅乱视听,信口攀扯的污衊之词。”
“孙儿內帷之事,自有分寸,不劳她一个外人妄加揣测,更不屑以此等荒唐藉口,行要挟逼迫之实。”
他顿了顿,再次向老夫人躬身,这一次,话语中的决绝如同出鞘的寒铁,再无丝毫转圜余地:
“祖母今日为孙儿主持公道,所言『怨偶非福』、『家宅寧和为上』,孙儿字字铭记於心,不敢或忘。”
“只是——”
他抬起头,目光如炬,声音冷凝而坚定:
“孙儿此生,寧娶布衣贤女,荆釵布裙,相敬如宾;”
“也绝不容中山之狼,披锦绣华服,登堂入室,貽害门庭!”
“你口口声声,为我那莫须有的心上人著想,处处体贴,甚至『甘愿』贬妻为妾……”
“我倒要问问你,我江凌川,何时与你透露过半句,我有什么所谓的心上人?!”
“你这般言之凿凿,是在替我认下什么风流债,还是在凭空污我清誉,臆测我內帷不修,私德有亏?”
“你既已知错,便该诚心悔过,静思己过。如何悔过,自有家法规矩裁定。”
“而不是在这里,以退为进,搬弄是非,顛倒黑白,搅得家宅不寧,让长辈烦心!”
江凌川对著老夫人和孟氏,郑重一揖到底,声音沉痛决绝:
“祖母,母亲明鑑!”
“此女,婚前便已失手伤姐,德行有亏;身边奴僕亡故事出蹊蹺,惹人非议,已损及自身与家族清誉;”
“如今,更因莫须有的妒忌,竟敢在长辈面前,妄言自贬,搅乱伦常,视婚姻礼法如无物!”
“桩桩件件,皆已证明其品行不端,心术不正!”
他抬起头,目光如炬,斩钉截铁:
“敢问祖母、母亲——”
“如此不堪之人,如何还能再为我侯府之媳?!”
杨令薇闻言,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衝上了头顶,又瞬间冻结。
她跪在地上的五指猛地收紧。
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,才勉强维持住摇摇欲坠的身体。
她猛地抬头,望向江凌川的眼神里,是再也掩饰不住的恨意与疯狂。
他怎么敢!
怎么敢在长辈面前,如此不留情面地彻底否定她!
孟氏也被江凌川这毫不留情的决绝姿態惊了一下。
下意识地看向主位的老夫人。
老夫人面色沉凝如水,眉头紧锁,手中佛珠捻动的速度不自觉地加快。
她的目光在跪在地上形容狼狈的杨令薇,与躬身作揖態度决然的孙子之间,来回逡巡。
厅內空气仿佛凝固,只余下压抑的呼吸声。
半晌,老夫人长长地嘆息了一声。
“哎……”
老夫人缓缓开口,声音带著久经世事的疲惫,但语气却坚决,她道,
“常言道,家门娶妇,德行为先。今日,无论杨四小姐所言是真是假,是实是虚。”
“你们二人之间……怨懟已深,性情难合,已是明摆著的事实了。”
她看向杨令薇,目光复杂,但其中的疏离与否定清晰可见:
“如此情形,纵使勉强成婚,也绝非佳偶天成,只怕要成一对怨偶,终日爭执,家宅不寧……”
“这绝非家族之福,亦非你二人之幸。”
老夫人顿了顿,语气更沉,一锤定音:
“此事,关乎两府顏面与子弟终身,已非老身一人可独断。”
“杨小姐,你……今日先回去罢。”
杨令薇闻言,如遭雷击,浑身剧震。
慌乱、不甘、恐惧的目光,瞬间投向了坐在老夫人下首的孟氏,眼中满是最后的祈求与暗示。
孟氏接收到了杨令薇那急切求救的眼神。
她眼睫微垂,避开了那目光,沉吟一瞬,才抬眼看向老夫人。
声音温和带著附和:
“母亲所言极是。结亲本是结两姓之好,守望相助。”
“若结亲反结成了仇,酿出怨偶,確是家门不幸。”
不过,她后面话锋一转,只道:
“只是……婚姻大事,终究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。”
“此事体大,还需侯爷回府之后,与杨家老爷当面细细商议,方能最终定夺。”
说罢,孟氏这才將目光重新投向地上脸色惨白、摇摇欲坠的杨令薇,语气是带著疏离的劝诫:
“杨四小姐,今日你也听了,也说了。且先回去,平心静气,好生……反省己过。”
她特意在“反省”二字上略略加重,目光意味深长:
“若真有错,需得真心懺悔,切实改过,方是……立身之正道。”
“回去,也將老夫人的意思,细细稟明你父母吧。”
杨令薇听著大夫人那番话。
只觉得浑身力气瞬间被抽空,四肢百骸一阵酸软,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微微晃了一下,几乎瘫软在地。
完了……
她脑中一片轰鸣,事到如今,竟还是要走到退婚这一步吗?!
不,她不甘心!
她猛地抬头想爭辩。
却对上大夫人孟氏制止的眼神。
杨令薇胸口剧烈起伏,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。
最终还是在那无声的威压下,认命地闭上了嘴。
所有的怨恨、不甘、疯狂,都被强行压回心底,化作更深的毒。
她踉蹌著,几乎是被身旁的丫鬟丁香半拖半扶地架了起来。
她对著上首的老夫人和孟氏,用尽最后力气,行了一个失魂落魄的礼,声音低哑破碎:
“令薇……告退。”
厅內只剩自家人。
江凌川没走。
他就那么静静地立在原地,身姿笔挺,目光幽沉,周身散发著尚未散尽的寒意。
正厅內一时静得落针可闻,只有香炉里细烟裊裊。
老夫人看著他,眼中带著疲惫,也有一丝复杂难辨的情绪。
她捻动佛珠的手停下,缓缓开口,声音比方才更显苍老:
“二郎。”
江凌川闻声,终於有了动作。
他上前一步,对著老夫人深深一揖,姿態恭谨,脊背挺得笔直。
“祖母。”
老夫人看著他低垂的头顶,嘆了口气:
“今日……你也看到了。杨家这门亲事,怕是难了。只是……”
她顿了顿,目光带著审视,
“方才杨四丫头口中,你那『心上人』……是怎么回事?”
孟氏也抬起眼,目光落在江凌川身上,带著惯常的温和,以及一丝不宜察觉的探究。
江凌川缓缓直起身,迎上老夫人的目光,脸上一片坦然的沉静。
他开口,声音清晰,字字分明,既是回答,也是宣告:
“回祖母,孙儿並无什么『心上人』。”
他目光扫过一旁同样注视著他的孟氏,语气平淡却斩钉截铁:
“不过是杨氏为遮掩自身罪愆、搅乱视听,信口攀扯的污衊之词。”
“孙儿內帷之事,自有分寸,不劳她一个外人妄加揣测,更不屑以此等荒唐藉口,行要挟逼迫之实。”
他顿了顿,再次向老夫人躬身,这一次,话语中的决绝如同出鞘的寒铁,再无丝毫转圜余地:
“祖母今日为孙儿主持公道,所言『怨偶非福』、『家宅寧和为上』,孙儿字字铭记於心,不敢或忘。”
“只是——”
他抬起头,目光如炬,声音冷凝而坚定:
“孙儿此生,寧娶布衣贤女,荆釵布裙,相敬如宾;”
“也绝不容中山之狼,披锦绣华服,登堂入室,貽害门庭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