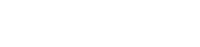福安堂的小茶房內,唐玉心绪不寧,惶恐未定。
而另一边的寒梧苑,练武场中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唰——!鏘!嚓!
刀光如练,破空之声凌厉刺耳。
江凌川赤裸著精壮的上身,只著一条黑色绸裤。
手中一柄制式绣春刀被他舞得寒光四射,杀气腾腾。
他招式毫无花哨,每一刀都倾尽全力。
带著一股欲要劈开眼前一切阻碍的狠戾与狂暴。
轰——!
又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斜劈,刀刃深深嵌入用作靶子的包铁木桩。
竟硬生生將碗口粗的坚硬木桩从中劈裂开来,木屑纷飞!
一块崩飞的碎木携著劲风,直朝场边侍立的江平面门射来。
江平眼皮一跳,身形敏捷地朝旁一侧。
碎木“咚”地一声砸在他身后的青砖墙上,险险避过。
江平心有余悸地摸了摸鼻子。
看著场中的男人,心中暗暗叫苦。
他今日守在正厅外,將里面的交锋听了个七七八八。
谁能想到,那杨家四小姐胆大包天至此,竟真不是来服软退婚的!
反而以退为进,自曝“小错”以掩“大恶”。
最后更是丧心病狂,竟敢拿文玉姑娘作要挟。
竟逼得二爷投鼠忌器,连那买凶的罪证都无法当场说出!
这简直是触碰二爷的逆鳞!
也难怪二爷此刻窝火不满。
幸好……老夫人终究是心疼孙儿的。
她態度鲜明,不愿看到孙子与那样一个女人绑在一起。
这门婚事,应该……能退掉了吧?
江平心里刚冒出这个念头,稍稍鬆了口气。
“江平!”
场中骤然传来一声冰冷低喝,打断了江平的思绪。
“与我对练!”
江平头皮一麻,看著二爷那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眼神。
只得苦著脸,硬著头皮,从兵器架上取下一柄未开刃的练习用刀。
咬紧牙关,踏步上场。
接下来的小半个时辰,对江平而言不啻於一场酷刑。
江凌川的刀又快又重,招招逼人,
虽未用开刃的绣春刀,但那力道和速度,震得江平虎口发麻,手臂酸软,只能勉力招架,毫无还手之力。
就在江平觉得自己的手臂快要失去知觉时。
江凌川终於像是瞥见了他的窘態,刀势一收,不再追击。
他不再看江平,转而独自一人。
又將那套凌厉的刀法从头至尾,一丝不苟地演练了十几遍。
每一招每一式都灌注了全力。
汗水如同小溪般从他賁张的胸肌、块垒分明的腹肌上滚落,浸湿了绸裤。
猎豹般矫健的臂膀、胸膛上泛著水光。
直到气息微促,汗出如浆,江凌川才“鏘”的一声,还刀入鞘。
结束了这场近乎自虐般的演练。
他没有立刻去擦汗,而是站在场中,闭目调息了片刻。
任由晚风吹拂过滚烫的皮肤。
然后,他径直走向旁边的井台,提起一桶刚从深井中打上来的冷水。
那水还冒著丝丝寒气。
隨即从头到脚,兜头浇下。
哗啦——!
冰冷刺骨的井水冲走了满身的燥热与汗渍,也仿佛浇熄了些许翻腾的怒火。
水珠顺著他黑髮、下頜和锁骨不断滴落。
他甩了甩头,水珠四溅。
然后抓起一旁架子上乾燥的布巾,隨意擦了擦。
便套上一件乾净的深色常服,转身朝书房走去。
书房內,烛火已亮。
江凌川散著微湿的头髮,坐在书案后,手指无声捻动。
他面色沉静,目光幽深地望著跳动的烛火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江平轻手轻脚地进来,奉上一盏温热的参茶,覷著他的脸色,小心翼翼地开口:
“二爷……可是还在思量今日杨家退婚之事?”
他斟酌著语气道,
“小的觉著,二爷倒不必过於忧心了。那杨四小姐今日……简直是自掘坟墓。”
“桩桩件件,劣跡斑斑,又闹得府中女眷皆知。”
“就算侯爷和大夫人再情愿这门亲事,眼见如此,想来……也不会再坚持这门亲事了吧?”
江平劝慰的话音刚落,江凌川就抬起眼。
目光幽深地看向江平,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冷嗤。
“祖母的態度,是意料之中,也是目前能爭取到的最好局面。”
他声音平稳,却冰冷,
“但若以为,仅凭祖母今日几句话,这婚便能顺顺噹噹退掉……那是痴心妄想。”
他身体微微后靠,倚进圈椅中,烛火在他深邃的眸中跳跃,映出一片寒光:
“最终,还是要看『利益』二字,在父亲心中的分量,孰轻孰重。”
“父亲他……”
江凌川顿了顿,语气带著讥誚与瞭然,
“他从不在乎杨氏是否『贤良淑德』,他只在乎,杨家这门姻亲是否还『可用』。”
“只想著撕毁婚约的代价,是否在他承受范围之內,又或者……能否换来更大的利益。”
“今日这一闹,表面是內帷失和,实则是与杨家彻底撕破脸皮。”
他眸光转冷,
“接下来,还不知道父亲要如何转圜。”
江凌川不再看江平,目光重新落回虚空。
片刻,他再次开口,声音更低,带著决断:
“不过,坐等父亲权衡,非我风格。杨家的把柄……远不止今日她自曝的这几桩。”
他倏地抬眼,目光如电射向江平:
“江平,你记著。”
“第一,杨令薇虐杀奴僕一事,她今日虽狡辩是病故,但这本就是胡扯。”
“立刻加派人手,不惜代价,找到当年那个香禾的家人、为她诊过病的所谓大夫、以及庄子上的知情庄头或僕役。”
“找到后,不必带回京,就地妥善保护起来,確保他们安全,也確保他们到时候能说该说的话。”
“第二,从正在查办的『白莲教案』里,分出两个机灵可靠、嘴巴严实的人手。”
“不必大张旗鼓,但要正式立案,暗中详查杨御史近三年在漕运、盐引,乃至工部河工款项上的所有经手帐目与人情往来。”
“我要確凿的、能摆上檯面的东西,哪怕只是疑似、关联,也要查得清清楚楚。”
他一口气说完,节奏平稳,却带著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。
最后,他缓缓抬起眼眸,眼中再无半分犹豫与温度。
只剩下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与狩猎般的锐利。
他极轻地扯了一下嘴角,那笑意冰冷刺骨,
“她想玩……”
“那爷便陪她玩……”
而另一边的寒梧苑,练武场中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唰——!鏘!嚓!
刀光如练,破空之声凌厉刺耳。
江凌川赤裸著精壮的上身,只著一条黑色绸裤。
手中一柄制式绣春刀被他舞得寒光四射,杀气腾腾。
他招式毫无花哨,每一刀都倾尽全力。
带著一股欲要劈开眼前一切阻碍的狠戾与狂暴。
轰——!
又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斜劈,刀刃深深嵌入用作靶子的包铁木桩。
竟硬生生將碗口粗的坚硬木桩从中劈裂开来,木屑纷飞!
一块崩飞的碎木携著劲风,直朝场边侍立的江平面门射来。
江平眼皮一跳,身形敏捷地朝旁一侧。
碎木“咚”地一声砸在他身后的青砖墙上,险险避过。
江平心有余悸地摸了摸鼻子。
看著场中的男人,心中暗暗叫苦。
他今日守在正厅外,將里面的交锋听了个七七八八。
谁能想到,那杨家四小姐胆大包天至此,竟真不是来服软退婚的!
反而以退为进,自曝“小错”以掩“大恶”。
最后更是丧心病狂,竟敢拿文玉姑娘作要挟。
竟逼得二爷投鼠忌器,连那买凶的罪证都无法当场说出!
这简直是触碰二爷的逆鳞!
也难怪二爷此刻窝火不满。
幸好……老夫人终究是心疼孙儿的。
她態度鲜明,不愿看到孙子与那样一个女人绑在一起。
这门婚事,应该……能退掉了吧?
江平心里刚冒出这个念头,稍稍鬆了口气。
“江平!”
场中骤然传来一声冰冷低喝,打断了江平的思绪。
“与我对练!”
江平头皮一麻,看著二爷那没有丝毫商量余地的眼神。
只得苦著脸,硬著头皮,从兵器架上取下一柄未开刃的练习用刀。
咬紧牙关,踏步上场。
接下来的小半个时辰,对江平而言不啻於一场酷刑。
江凌川的刀又快又重,招招逼人,
虽未用开刃的绣春刀,但那力道和速度,震得江平虎口发麻,手臂酸软,只能勉力招架,毫无还手之力。
就在江平觉得自己的手臂快要失去知觉时。
江凌川终於像是瞥见了他的窘態,刀势一收,不再追击。
他不再看江平,转而独自一人。
又將那套凌厉的刀法从头至尾,一丝不苟地演练了十几遍。
每一招每一式都灌注了全力。
汗水如同小溪般从他賁张的胸肌、块垒分明的腹肌上滚落,浸湿了绸裤。
猎豹般矫健的臂膀、胸膛上泛著水光。
直到气息微促,汗出如浆,江凌川才“鏘”的一声,还刀入鞘。
结束了这场近乎自虐般的演练。
他没有立刻去擦汗,而是站在场中,闭目调息了片刻。
任由晚风吹拂过滚烫的皮肤。
然后,他径直走向旁边的井台,提起一桶刚从深井中打上来的冷水。
那水还冒著丝丝寒气。
隨即从头到脚,兜头浇下。
哗啦——!
冰冷刺骨的井水冲走了满身的燥热与汗渍,也仿佛浇熄了些许翻腾的怒火。
水珠顺著他黑髮、下頜和锁骨不断滴落。
他甩了甩头,水珠四溅。
然后抓起一旁架子上乾燥的布巾,隨意擦了擦。
便套上一件乾净的深色常服,转身朝书房走去。
书房內,烛火已亮。
江凌川散著微湿的头髮,坐在书案后,手指无声捻动。
他面色沉静,目光幽深地望著跳动的烛火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江平轻手轻脚地进来,奉上一盏温热的参茶,覷著他的脸色,小心翼翼地开口:
“二爷……可是还在思量今日杨家退婚之事?”
他斟酌著语气道,
“小的觉著,二爷倒不必过於忧心了。那杨四小姐今日……简直是自掘坟墓。”
“桩桩件件,劣跡斑斑,又闹得府中女眷皆知。”
“就算侯爷和大夫人再情愿这门亲事,眼见如此,想来……也不会再坚持这门亲事了吧?”
江平劝慰的话音刚落,江凌川就抬起眼。
目光幽深地看向江平,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冷嗤。
“祖母的態度,是意料之中,也是目前能爭取到的最好局面。”
他声音平稳,却冰冷,
“但若以为,仅凭祖母今日几句话,这婚便能顺顺噹噹退掉……那是痴心妄想。”
他身体微微后靠,倚进圈椅中,烛火在他深邃的眸中跳跃,映出一片寒光:
“最终,还是要看『利益』二字,在父亲心中的分量,孰轻孰重。”
“父亲他……”
江凌川顿了顿,语气带著讥誚与瞭然,
“他从不在乎杨氏是否『贤良淑德』,他只在乎,杨家这门姻亲是否还『可用』。”
“只想著撕毁婚约的代价,是否在他承受范围之內,又或者……能否换来更大的利益。”
“今日这一闹,表面是內帷失和,实则是与杨家彻底撕破脸皮。”
他眸光转冷,
“接下来,还不知道父亲要如何转圜。”
江凌川不再看江平,目光重新落回虚空。
片刻,他再次开口,声音更低,带著决断:
“不过,坐等父亲权衡,非我风格。杨家的把柄……远不止今日她自曝的这几桩。”
他倏地抬眼,目光如电射向江平:
“江平,你记著。”
“第一,杨令薇虐杀奴僕一事,她今日虽狡辩是病故,但这本就是胡扯。”
“立刻加派人手,不惜代价,找到当年那个香禾的家人、为她诊过病的所谓大夫、以及庄子上的知情庄头或僕役。”
“找到后,不必带回京,就地妥善保护起来,確保他们安全,也確保他们到时候能说该说的话。”
“第二,从正在查办的『白莲教案』里,分出两个机灵可靠、嘴巴严实的人手。”
“不必大张旗鼓,但要正式立案,暗中详查杨御史近三年在漕运、盐引,乃至工部河工款项上的所有经手帐目与人情往来。”
“我要確凿的、能摆上檯面的东西,哪怕只是疑似、关联,也要查得清清楚楚。”
他一口气说完,节奏平稳,却带著一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。
最后,他缓缓抬起眼眸,眼中再无半分犹豫与温度。
只剩下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与狩猎般的锐利。
他极轻地扯了一下嘴角,那笑意冰冷刺骨,
“她想玩……”
“那爷便陪她玩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