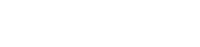接下来的两天,马修忙得像个陀螺。
他在宾大的校园论坛、推特以及各大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志愿者招募公告。不得不说,肖恩·潘这个名字如今在年轻人中確实有號召力。不到24小时,报名表就塞满了邮箱。
经过筛选,马修留下了一批志愿者。这群年轻人大多是法学院或政治学系的学生,充满热情且廉价……
甚至免费!
他们一部分被分配给文森特,帮忙处理那些繁琐的法律文书检索工作;还有一部分拿著问捲走上街头,去收集最基层的民意数据。
在肖恩离开宾州之后,他们將作为有生力量继续存在。
但这还不够。
对於一场正经的竞选来说,这些志愿者只能算是步兵。肖恩真正缺少的,是能够运筹帷幄的“军师”,是那种懂政治交易的老手。
而肖恩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。不过因为他另有要务,所以由马修来负责接触这一人物。
此刻,南街的一家老式咖啡馆里,空气中瀰漫著烘焙咖啡豆的焦香。
马修坐在靠窗的位置,侷促地搅拌著面前的拿铁。而在他对面,乔治·凯利正戴著老花镜,用一根手指笨拙地划拉著手机屏幕。
“两百三十万粉丝……”凯利看著推特上的数字,嘖嘖称奇,“这还是个刚註册不到三个月的帐號。肖恩·潘很壮啊!”
感嘆完之后,他放下手机,摘下眼镜,目光温和地投向马修。
“马修·陈,宾夕法尼亚大学歷史系的高材生。”凯利微笑著问,“告诉我,孩子,你未来想从政吗?”
马修停下搅拌的动作,思考了几秒。
“我还在观察,凯利先生。歷史告诉我们,政治是个大染缸,进去的人很少能干乾净净地出来。但我又觉得,如果不进去,就永远无法改变什么。”
“模稜两可,但很诚实。”凯利笑了笑,“你有从政的潜力。那种既想保持洁癖又不得不把手弄脏的纠结,我听说是每个优秀政治家的必经之路。”
“那么,说说看吧。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会加入这个草台班子?”
马修尷尬地挠了挠头:“其实……这是潘先生的意思。”
“哦?他怎么说的?”
“他说……”马修虽然犹豫了,还是决定实话实说,“他说您主动找上门来,要么是暗恋他,要么是想利用他。而这两者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——您会帮我们。”
说到最后,马修的脸都红了。这话从嘴里说出来,实在有点太自恋了。
凯利先是愣住,隨即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“哈哈哈哈!肖恩·潘,这小子还真敢想!”凯利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,“暗恋?我都快进棺材了!不过,关於利用这一点,他倒是没说错。”
笑过之后,凯利重新戴上眼镜,神色变得认真起来。
“他其实是看中了我身上的政治资源和人脉。对於他来说,我这个过气的老头子也许没什么大用,但既然我都送上门来了,他不介意在我身上花点时间,看看能不能榨出点剩余价值。不是吗?”
“这话虽然难听,但逻辑上没错。”马修也没否认他的话。
“肖恩是个天才。”凯利评价道,“他有著远超年龄的识人之明。他能分清谁喜欢他,谁不喜欢他,这种天赋,是很罕有的。”
“可是,我认为他在竞选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上,犯了大错。那就是意识形態。”
“意识形態?”
“没错。他自以为长袖善舞,可以在两党之间左右逢源,甚至想要超越党派,代表所谓的『纯粹民意』。”凯利摇了摇头,“但在美国的政治生態里,从来不存在真正的中间派。你要么是红的,要么是蓝的。如果你试图变成紫色,最后只会被两边一起撕碎。”
“真的吗?”马修忍不住反驳,“我觉得歷史是可以被创造的。也许肖恩能走出第三条路呢?”
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,孩子。”凯利看著他,“那你觉得,你自己的意识形態偏向什么?”
“或许是一种……新国家主义?”马修试探著说,“像老罗斯福那样,强化国家能力,遏制资本,保障公平。”
“西奥多啊……”凯利嘆了口气,“他確实是个伟人,但在这个时代,他已经过时了。或者说,现在的共和党已经不认他这个祖宗了。”
“当然,我可能更过时。”凯利自嘲地笑了笑,“我的意识形態,恐怕是你们没办法接受的。”
马修有些疑惑,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你知道我的真名吗?”凯利突然问道。
“不是乔治·凯利吗?”
“不,那是后来改的。”凯利轻声道,“我的本名是威士涅威茨基。那是我一位俄罗斯先祖的名字。而凯利,是那位先祖妻子的姓氏。她的全名叫弗洛伦斯·凯利。”
马修作为歷史系学生,脑子转得飞快。
“弗洛伦斯·凯利?那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?她是美国最早翻译卡尔和弗里德里希著作的人。”
“没错。”凯利点头,“他们后来离婚了,弗洛伦斯带著孩子回到了美国,但依然保留了夫姓。而我,就是那个家族的一员。”
马修看著眼前这个衣著考究的老人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“年轻的时候,我也曾是个激进的左翼分子。”凯利回忆道,“那时候的费城,比现在激进得多。我也改回了祖先的姓氏威士涅威茨基,以此为荣。”
“直到1985年,move组织被那场大火烧毁。”凯利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那场悲剧改变了一切。我也选择了『詔安』。我加入了民主党,开始玩那些骯脏的游戏。”
“我帮几任市长竞选成功,看著他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政客。直到『占领华尔街』运动爆发,我突然觉得累了。所以我选择了离开。”
凯利看著马修,眼神里装满了各种情绪。
“我的根底是红色的,孩子。哪怕我现在看起来像个温和的老头,但我的骨子里依然流著激进的血。”
“告诉我,这样的我是你们的敌人还是朋友?”
马修沉默了。
……
费城喜来登酒店,二楼宴会厅。
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发布会现场。台下坐满了记者,长枪短炮对准了台上那个空荡荡的讲台。
后台休息室里,肖恩正在整理领带。
丹尼尔·布朗推门进来,脸色依然不算好看。
“潘,那个薄荷菸头,鑑证科的结果出来了。”布朗开门见山,“上面虽然没有提取到完整的dna,但从唾液酶的活性来看,它是最近留下的。大概就在我们去现场的前三天左右。”
“那就是说,在我去现场之前,確实有人回去过。”
“没错。”布朗承认道,“这证实了你的推测:罪犯重返了现场。而且根据那个品牌的受眾分析,黑人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“那名单呢?”
“马库斯提供的名单我也查过了。”布朗皱起眉,“几百號人,绝大多数都有不在场证明。那天他们在工会搞烧烤派对……打牌,互相都能作证。只有几个人中途离开过,或者是请了病假没去。”
“那几个人查了吗?”
“正在查。但目前还没找到什么破绽。”布朗烦躁地说,“这就像大海捞针。”
“那就继续捞。”肖恩转过身,看著镜子里的自己,“別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哪怕是他们那天去买了包烟,或者给谁打了个电话。”
“你是在命令我吗?”布朗不爽地反问。
虽然他很不爽,但是他对肖恩的好感度已经只是【-10】了。
肖恩整理好领带,转过身,脸上掛著那种自信的微笑。
“如果可以,会有那么一天的,布朗警官。那个时候,我不只会命令你。”
布朗看著他,冷哼一声,没再说话。
“好了,我要上场了。”肖恩拍了拍布朗的肩膀,“记得在台下给我鼓掌。”
……
“咔嚓!咔嚓!”
当肖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,闪光灯连成了一片白昼。
他微笑著向台下挥手,从容得像是在走奥斯卡的红毯。
“下午好,各位媒体朋友,各位费城的市民。”
肖恩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,富有磁性且十分坚定。
“过去的两个月,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奇幻漂流。我从洛杉磯来到费城,原本只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。但我没想到,我会深深爱上这座城市。”
“我看到了唐人街的困境,所以我站了出来。我看到了社区被资本挤压的痛苦,所以我发出了声音。我很荣幸,我们成功了。76人队的新球馆计划暂时搁置,这不仅是我的胜利,更是每一个费城人的胜利!”
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。
“但是,”肖恩的神情变得严肃,“在这个过程中,我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污衊和攻击。”
“有人指控我煽动暴乱,有人说我为了竞选不择手段。甚至有人暗示,那场针对警车的袭击是我自导自演的闹剧。”
“对此,我只有一句话:我无所畏惧。”
肖恩双手撑在讲台上,目光扫视全场。
“因为我相信法律,我相信正义,更相信歷史的审判。我已经决定,与费城警方展开全面合作,不仅仅是为了洗清我自己的嫌疑,更是为了找到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,我向德拉瓦河起誓,我將还费城一个真相!
“我知道这条路很难。我知道会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,等著看我摔倒。但我不会退缩。因为我知道,我的身后站著你们!
“站著千千万万渴望改变、渴望公平的普通民眾!
“只要我们站在一起,就没有什么能打倒我们!
“谢谢大家!”
演讲结束,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
隨后的提问环节,肖恩更是对答如流,將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化作了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。
半小时后,发布会散场。
肖恩在保鏢的护送下走出宴会厅,感觉背后的衬衫都被汗水浸湿了。
就在他准备钻进电梯时,一个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那是个女人,穿著一件普通的米色风衣,戴著眼镜,没有掛记者证。
但肖恩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“肖恩,你……你不会指望著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就能把凶手钓出来把?”蕾切尔·琼斯气喘吁吁地看著肖恩。
“蕾切尔,你怎么在这里?你已经错过提问时间了!”肖恩没有正面回答她,反而露出一个柔和的微笑。“下一次我会给你准备一个真正的大新闻。”
而蕾切尔呆了一会儿,便尷尬道:“不用了,我被开除了。肖恩,现在是我要给你准备一个大新闻。”
他在宾大的校园论坛、推特以及各大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志愿者招募公告。不得不说,肖恩·潘这个名字如今在年轻人中確实有號召力。不到24小时,报名表就塞满了邮箱。
经过筛选,马修留下了一批志愿者。这群年轻人大多是法学院或政治学系的学生,充满热情且廉价……
甚至免费!
他们一部分被分配给文森特,帮忙处理那些繁琐的法律文书检索工作;还有一部分拿著问捲走上街头,去收集最基层的民意数据。
在肖恩离开宾州之后,他们將作为有生力量继续存在。
但这还不够。
对於一场正经的竞选来说,这些志愿者只能算是步兵。肖恩真正缺少的,是能够运筹帷幄的“军师”,是那种懂政治交易的老手。
而肖恩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选。不过因为他另有要务,所以由马修来负责接触这一人物。
此刻,南街的一家老式咖啡馆里,空气中瀰漫著烘焙咖啡豆的焦香。
马修坐在靠窗的位置,侷促地搅拌著面前的拿铁。而在他对面,乔治·凯利正戴著老花镜,用一根手指笨拙地划拉著手机屏幕。
“两百三十万粉丝……”凯利看著推特上的数字,嘖嘖称奇,“这还是个刚註册不到三个月的帐號。肖恩·潘很壮啊!”
感嘆完之后,他放下手机,摘下眼镜,目光温和地投向马修。
“马修·陈,宾夕法尼亚大学歷史系的高材生。”凯利微笑著问,“告诉我,孩子,你未来想从政吗?”
马修停下搅拌的动作,思考了几秒。
“我还在观察,凯利先生。歷史告诉我们,政治是个大染缸,进去的人很少能干乾净净地出来。但我又觉得,如果不进去,就永远无法改变什么。”
“模稜两可,但很诚实。”凯利笑了笑,“你有从政的潜力。那种既想保持洁癖又不得不把手弄脏的纠结,我听说是每个优秀政治家的必经之路。”
“那么,说说看吧。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会加入这个草台班子?”
马修尷尬地挠了挠头:“其实……这是潘先生的意思。”
“哦?他怎么说的?”
“他说……”马修虽然犹豫了,还是决定实话实说,“他说您主动找上门来,要么是暗恋他,要么是想利用他。而这两者都会导向同一个结果——您会帮我们。”
说到最后,马修的脸都红了。这话从嘴里说出来,实在有点太自恋了。
凯利先是愣住,隨即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“哈哈哈哈!肖恩·潘,这小子还真敢想!”凯利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,“暗恋?我都快进棺材了!不过,关於利用这一点,他倒是没说错。”
笑过之后,凯利重新戴上眼镜,神色变得认真起来。
“他其实是看中了我身上的政治资源和人脉。对於他来说,我这个过气的老头子也许没什么大用,但既然我都送上门来了,他不介意在我身上花点时间,看看能不能榨出点剩余价值。不是吗?”
“这话虽然难听,但逻辑上没错。”马修也没否认他的话。
“肖恩是个天才。”凯利评价道,“他有著远超年龄的识人之明。他能分清谁喜欢他,谁不喜欢他,这种天赋,是很罕有的。”
“可是,我认为他在竞选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上,犯了大错。那就是意识形態。”
“意识形態?”
“没错。他自以为长袖善舞,可以在两党之间左右逢源,甚至想要超越党派,代表所谓的『纯粹民意』。”凯利摇了摇头,“但在美国的政治生態里,从来不存在真正的中间派。你要么是红的,要么是蓝的。如果你试图变成紫色,最后只会被两边一起撕碎。”
“真的吗?”马修忍不住反驳,“我觉得歷史是可以被创造的。也许肖恩能走出第三条路呢?”
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,孩子。”凯利看著他,“那你觉得,你自己的意识形態偏向什么?”
“或许是一种……新国家主义?”马修试探著说,“像老罗斯福那样,强化国家能力,遏制资本,保障公平。”
“西奥多啊……”凯利嘆了口气,“他確实是个伟人,但在这个时代,他已经过时了。或者说,现在的共和党已经不认他这个祖宗了。”
“当然,我可能更过时。”凯利自嘲地笑了笑,“我的意识形態,恐怕是你们没办法接受的。”
马修有些疑惑,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“你知道我的真名吗?”凯利突然问道。
“不是乔治·凯利吗?”
“不,那是后来改的。”凯利轻声道,“我的本名是威士涅威茨基。那是我一位俄罗斯先祖的名字。而凯利,是那位先祖妻子的姓氏。她的全名叫弗洛伦斯·凯利。”
马修作为歷史系学生,脑子转得飞快。
“弗洛伦斯·凯利?那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?她是美国最早翻译卡尔和弗里德里希著作的人。”
“没错。”凯利点头,“他们后来离婚了,弗洛伦斯带著孩子回到了美国,但依然保留了夫姓。而我,就是那个家族的一员。”
马修看著眼前这个衣著考究的老人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“年轻的时候,我也曾是个激进的左翼分子。”凯利回忆道,“那时候的费城,比现在激进得多。我也改回了祖先的姓氏威士涅威茨基,以此为荣。”
“直到1985年,move组织被那场大火烧毁。”凯利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那场悲剧改变了一切。我也选择了『詔安』。我加入了民主党,开始玩那些骯脏的游戏。”
“我帮几任市长竞选成功,看著他们从理想主义者变成政客。直到『占领华尔街』运动爆发,我突然觉得累了。所以我选择了离开。”
凯利看著马修,眼神里装满了各种情绪。
“我的根底是红色的,孩子。哪怕我现在看起来像个温和的老头,但我的骨子里依然流著激进的血。”
“告诉我,这样的我是你们的敌人还是朋友?”
马修沉默了。
……
费城喜来登酒店,二楼宴会厅。
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发布会现场。台下坐满了记者,长枪短炮对准了台上那个空荡荡的讲台。
后台休息室里,肖恩正在整理领带。
丹尼尔·布朗推门进来,脸色依然不算好看。
“潘,那个薄荷菸头,鑑证科的结果出来了。”布朗开门见山,“上面虽然没有提取到完整的dna,但从唾液酶的活性来看,它是最近留下的。大概就在我们去现场的前三天左右。”
“那就是说,在我去现场之前,確实有人回去过。”
“没错。”布朗承认道,“这证实了你的推测:罪犯重返了现场。而且根据那个品牌的受眾分析,黑人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“那名单呢?”
“马库斯提供的名单我也查过了。”布朗皱起眉,“几百號人,绝大多数都有不在场证明。那天他们在工会搞烧烤派对……打牌,互相都能作证。只有几个人中途离开过,或者是请了病假没去。”
“那几个人查了吗?”
“正在查。但目前还没找到什么破绽。”布朗烦躁地说,“这就像大海捞针。”
“那就继续捞。”肖恩转过身,看著镜子里的自己,“別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哪怕是他们那天去买了包烟,或者给谁打了个电话。”
“你是在命令我吗?”布朗不爽地反问。
虽然他很不爽,但是他对肖恩的好感度已经只是【-10】了。
肖恩整理好领带,转过身,脸上掛著那种自信的微笑。
“如果可以,会有那么一天的,布朗警官。那个时候,我不只会命令你。”
布朗看著他,冷哼一声,没再说话。
“好了,我要上场了。”肖恩拍了拍布朗的肩膀,“记得在台下给我鼓掌。”
……
“咔嚓!咔嚓!”
当肖恩走上讲台的那一刻,闪光灯连成了一片白昼。
他微笑著向台下挥手,从容得像是在走奥斯卡的红毯。
“下午好,各位媒体朋友,各位费城的市民。”
肖恩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,富有磁性且十分坚定。
“过去的两个月,对我来说像是一场奇幻漂流。我从洛杉磯来到费城,原本只是为了寻找新的生活。但我没想到,我会深深爱上这座城市。”
“我看到了唐人街的困境,所以我站了出来。我看到了社区被资本挤压的痛苦,所以我发出了声音。我很荣幸,我们成功了。76人队的新球馆计划暂时搁置,这不仅是我的胜利,更是每一个费城人的胜利!”
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。
“但是,”肖恩的神情变得严肃,“在这个过程中,我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污衊和攻击。”
“有人指控我煽动暴乱,有人说我为了竞选不择手段。甚至有人暗示,那场针对警车的袭击是我自导自演的闹剧。”
“对此,我只有一句话:我无所畏惧。”
肖恩双手撑在讲台上,目光扫视全场。
“因为我相信法律,我相信正义,更相信歷史的审判。我已经决定,与费城警方展开全面合作,不仅仅是为了洗清我自己的嫌疑,更是为了找到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,我向德拉瓦河起誓,我將还费城一个真相!
“我知道这条路很难。我知道会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,等著看我摔倒。但我不会退缩。因为我知道,我的身后站著你们!
“站著千千万万渴望改变、渴望公平的普通民眾!
“只要我们站在一起,就没有什么能打倒我们!
“谢谢大家!”
演讲结束,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
隨后的提问环节,肖恩更是对答如流,將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化作了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。
半小时后,发布会散场。
肖恩在保鏢的护送下走出宴会厅,感觉背后的衬衫都被汗水浸湿了。
就在他准备钻进电梯时,一个身影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那是个女人,穿著一件普通的米色风衣,戴著眼镜,没有掛记者证。
但肖恩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“肖恩,你……你不会指望著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就能把凶手钓出来把?”蕾切尔·琼斯气喘吁吁地看著肖恩。
“蕾切尔,你怎么在这里?你已经错过提问时间了!”肖恩没有正面回答她,反而露出一个柔和的微笑。“下一次我会给你准备一个真正的大新闻。”
而蕾切尔呆了一会儿,便尷尬道:“不用了,我被开除了。肖恩,现在是我要给你准备一个大新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