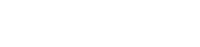第1072章 忽有狂徒夜磨刀,帝星飘摇荧惑高
大年初一,年关刚过,作为大明国都的应天城,本应喜气洋洋,此刻却被一股凝固氛围笼罩。
朝堂与民间皆是如此,就连走在街上的百姓都多了几分忧心忡忡,说话不敢大声,生怕被巡逻禁军盯上。
相较於以往,禁军比年前多了数倍不止,四方城门更是封锁得严严实实,但凡有半点身份瑕疵,就休想出城,甚至会被扣押审问。
一切的缘由,百姓们心知肚明,昨日皇城方向升起的黑色烟柱,人人都看在眼里。
谁都知道,祭天之时,皇宫附近失了火。
这等开年即至的不祥之兆,让所有人噤若寒蝉,不敢多提,更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不仅民间百姓茫然,朝中诸位大臣也同样不明所以。
他们只知道火是莫名其妙燃起的,不仅都督府著了火,浦子口城也未能倖免。
这两处皆是应天最重要的军事重地,甚至堪称天下武將嚮往之地,如今两地同时失火,还偏偏选在祭天之时,容不得人不多想。
是武將有反心?还是有人见不得武將好?
临近上午,皇城內的气氛依旧压抑,中军都督府门前,徐辉祖身著甲冑,手握长刀,脸色凝重地望著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杂物房。
一旁的曹国公李景隆亦是如此。
微风轻拂,带著几分冷冽与萧瑟,空气中的焦湖味似乎更重了些。
李景隆看著前方残垣断壁中忙碌整理的都督府吏员,嘴角勾起一抹讥讽,淡淡道:“刚回京就见到这一幕,真是热闹。”
徐辉祖深吸一口气,又重重吐出,诧异地看了一眼李景隆。
相较於两年前,九江显然成熟了许多,一举一动都透著大人风范,不再是往日的毛躁模样。
“现在知道京中局势了吧?
祭天这等大日子,都有人敢捣乱,真是胆大包天。”
李景隆神色微妙,轻声发问:“查到什么了吗?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,神情愈发微妙:“什么都没有查到,似乎逆党只是为了放火,给朝廷一个下马威,或者说,给陛下一个下马威。”
李景隆眉头紧皱,这一日他已听闻关於太子的诸多內情,轻声道:“太子莫名其妙中毒,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下马威?”
徐辉祖听出了他话中的深意,反问道:“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?”
李景隆在中军都督府门前渡了两步,又看向不远处的左军都督府,面露思索:“行军打仗,讲究一石二鸟,甚至一石三鸟,如今逆党这般行事,或许不只是为了破坏祭天,说不定还有別的目的。
说到这里,他抬头追问:“烧毁了什么东西?或许能从烧毁的物件中能察觉到些许端倪。”
徐辉祖闻言,面露讚嘆,忍不住点了点头:“九江,你真的长大了。”
李景隆脸色一黑,没有说话,只是用眼神催促他继续。
徐辉祖笑了笑,缓缓道:“中军都督府烧了杂物房,里面放著一些废弃的文书,左军都督府烧毁了从洪武十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一应军事调动,以及受封將领的人员名单。
浦子口城也被烧毁了小半个案牘库,同样是军事调动、人员名单以及粮草辐重的运输路线,对了,还有朝廷在各处官道旁设立的储粮点位置。
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推测,逆党是想烧毁这些军事文书,以此掩盖边军吃空餉、肆意挪用粮仓粮食的事实。”
李景隆听后眉头一皱,思索片刻道:“我在西北这两年,虽也见过吃空餉、掏空粮仓之事,但都是极少数,若是仅仅为了这些,逆党就要烧毁整个案牘库,那边军得有多少粮仓被掏空?又有多少人吃空餉?
我想,若非达到半数之多,没人会冒这般风险。”
徐辉祖点头附和: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诸位侯爷也觉得此事不合常理,但除此之外,实在没有別的解释。”
“锦衣卫怎么说?”李景隆反问,“事情都发生快一日了,锦衣卫难道还没查到端倪?”
徐辉祖脸色有些古怪,眼神中甚至带著一丝讥讽,轻轻摇了摇头:“锦衣卫现在自顾不暇。”
“为何?”
“锦衣卫的秘狱也著火了,同样烧毁了储存的军事文书。”
“什么?”
李景隆惊呼出声,眼睛猛地瞪大,连忙追问:“是城北那个秘狱?那里也有文书备份?”
徐辉祖诧异地看了他一眼:“这你都知道?”
李景隆脸色一黑:“应天城是我爹主持重建的,我怎么会不知道?”
徐辉祖忽然笑了起来,点头道:“也是,就是你说的那个秘狱,那里当初是检校秘密关押犯人的地方,现在被锦衣卫接管,不少绝密文书都藏在里面,甚至还有一个大牢,靖寧侯就关在那。”
此话一出,李景隆脸色凝重到了极点。
他比谁都清楚应天城的弯弯绕绕,锦衣卫秘狱的位置,除了锦衣卫內部,整个应天城的权贵中知晓者屈指可数,皆是位高权重之辈。
如今秘狱的文书都被烧了,这背后是谁?又为了什么?
想到这里,李景隆压低声音,仅让两人听见:“会不会是逆党想要作乱,藉此烧毁人员密档,好將自己的人瞒下来?以后谋逆?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:“知道秘狱位置的人就那么多,有胆子在祭天之日三处同时动手的,也就那么几位。
对他们而言,亲信下属遍布大明,根本无须隱瞒,就算要瞒,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”
李景隆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三道人影,凉国公蓝玉、宋国公冯胜、颖国公傅友德。
军中能有这般胆子与能力,同时在三处动手的,或许只有这三人,他又看了看自己,再看了看徐辉祖,若是他们的父亲还在世,也能轻鬆做到,但他们如今还没有这般实力。
“这么说来,此事是查不出结果了?”
徐辉祖耸了耸肩,嘆了口气,无奈点头:“既然人家敢做,就不怕被查,再说了,就算查到了又如何?”
李景隆一愣,很快便反应过来。
如今这等局势,三司巴不得什么都查不出来。
若是真查出哪位国公想要谋反,事情只会更加复杂,局势將变得烈火烹油。
但他转念一想,又觉得不能不查:“就算现在不挑破,也得把幕后真凶查出来,日后再做清算,有调查方向吗?”
徐辉祖神情有些微妙,轻轻点头:“今早毛驤递上来一封文书,上面列出了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各类战事的主要將领。
我仔细看了看,死的死,病的病,还有一些背负谋反骂名,剩下的已经没几个了。”
“还有谁?”
李景隆眼睛眯了起来。
“凉国公、宋国公、颖国公、开国公、西平侯、全寧侯、定远侯、长兴侯、武定侯、
怀远侯,以及俞通渊和陆云逸。”
徐辉祖的声音越来越轻,像是提及了什么禁忌之事。
李景隆越听,脸色越是凝重,反问道:“只有这些?不是还有其他將领吗?耿忠、冯诚、寧正不也都活得好好的。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:“这是锦衣卫筛选出的名单,毛驤认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些。
当然,冯诚也有这个本事,但他远在云南,从不掺和朝廷之事,所以不在此列。”
李景隆脸色顿时变得古怪:“那云逸也不在京城啊。”
徐辉祖眼睛眯了起来,淡淡道:“按照毛驤的说法,他虽人不在京城,但应天商行、建筑商行、水泥商行都在。
这等垄断京畿商脉的庞然大物,无数人从中获利,他想要串联一些人,再容易不过。
甚至在毛驤给出的名单中,除了最前面几位国公侯爷,就是他了。”
“妈的,这毛驤果然不是个好东西!”
李景隆破口大骂,“他这是公报私仇!”
作为曹国公,他知晓毛驤能官復原职,全靠云逸向太子进言。
如今这把刀非但不砍向別人,反而对准了自己人,实在荒谬!
徐辉祖面露无奈:“锦衣卫的推测也並非毫无道理。”
“他们推测了什么?”
徐辉祖拉著李景隆离开中军都督府衙门口,走到稍远些的城墙根下,轻声道:“毛驤猜测,这是凉国公在对陛下表示不满,凉国公是幕后主使,真正动手的人是陆云逸。”
李景隆瞳孔骤然收缩:“胡言乱语,空口无凭!他为何这般说?”
“陛下对於京中逆党一退再退,太子殿下的病情也不见好转。”徐辉祖解释道,“凉国公已经几次在朝会上破口大骂茹等人,说他们是谋害太子的逆党,请陛下惩处,但陛下始终没有行动,凉国公才会以此表示不满。”
此话一出,李景隆眉头皱得更紧,眼中闪过一丝荒谬:“这毛驤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?
凉国公若是痛恨谋害太子的逆党,为何不直接对那些人下手,反而要对陛下表示不满?”
徐辉祖忽然笑了起来,伸手揉了揉眉心,面露愁容:“你怎么知道他没动手?
你刚回京,有些事情还没来得及知晓。
最近这些日子,京城的夜里可不太平,茹等权贵的府邸常常有歹人作祟,要么是流窜多年的盗匪,要么是通缉已久的流寇。
他们总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京城,潜入这些大人物的府邸。
若非府邸防卫森严,锦衣卫也出手相助,这些人早就死了。
听答儿麻说,锦衣卫在各个府邸的暗线已经暴露了不下百人,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贵。”
“这...还有这种事?”
李景隆拳头猛地紧握,呼吸急促起来。
京中的斗爭比他想像得还要可怕,竟然已经到了直接杀人的地步。
这在大明朝立国二十多年来,也只发生过寥寥数次。
徐辉祖继续道:“军中也有异动,西城门守將莫名其妙被替换,其部下五百人被调回浦子口城。
新调来的千户王子文,表面上与凉国公毫无关联,但调令是后军都督府事陈然所发,他十年前曾与凉国公一同出征西番,担任前锋。”
李景隆只觉得嘴唇莫名乾涩,反问:“这是要谋反?”
他又想了想,问道:“朝廷已经认定此事是凉国公和陆云逸所为?”
看到他的表情,徐辉祖挥了挥手,勉强挤出一丝笑容:“锦衣卫只是推测,丕无实据,毛驤与答儿麻也不敢乱说,是我逼问,他们才透露的。
与凉国公有著同样嫌疑的,还有宋国公与潁国公,他们都与驻外藩王有姻亲关係。
若是太子真有不测,他们未必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思。”
此话一出,李景隆浑身汗毛倒竖,连忙看向四周,低声喝道:“慎言!这里是皇城!”
徐辉祖显然也意识到不妥,悻悻然摆了摆手,有些疲惫地开口:“最近的事情太多,一时失言,虽然不能明说,但京中不少人已经有了夺储的心思。
有人押注皇子,有人押注两个小殿下,变之乱成一团。”
“就没有盼著太子好转的?”
“有,但盼著太子不好的人更多。”徐辉祖道,“太子在时,天下安定,没人敢生出歪心思。
可现在太子抱恙,就算是原蜡安稳乔日的人,心中也难免胡思乱想。
有些念头一旦升起,就再也收不回去了。”
李景隆忽然想起一事,浑身紧绷:“你昨天问我秦王...秦王怎么了?他也有竭储之心?”
“不清楚。”徐辉祖摇头,“但坊间已经有了一些流言蜚语,太子在秦王的封地遭遇纵火,如丑又久病不起,秦王身为老二,容不得人不多想。”
“这等流言,必然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!”
徐辉祖点了点头:“必然的,神宫监最近与市易司走得很近,正在严查这些流言,也抓了不少人。
他们都老实交代了,是受人指使,拿了银子帆播的,但具体是谁指使的,却查不出来。”
“市易司也查不出来?”李景隆有些诧异。
他业控著新马商行,仅凭这一家商行,就知晓许多京城权贵都不知道的秘闻。
而牵史百万人生计的应天商行,理应知道得更多。
“能查得到源头,但...”徐辉祖顿了顿,“幕后之人太过狠辣,每当有新流言冒出来,神烈山的乱坟岗上就会多几具尸体,想来都是最先传播流言的人。
神宫监每每查到这里,线索就戛然而止。”
李景隆站在墙根下,双手叉,看著前方忙碌的吏员与军卒。
眼前的景乌看兄安定,他却能感受到暗流涌动,让他坐立不安:“咱们能做什么?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:“像你我这般勛贵后继,最好不要掺和这些事。
你我与国同休,只要不捲入纷爭,不论將来是谁登基,都少不了你我的富贵,我最怕你一时衝动做了傻事,切烧谨言慎行。”
“现在京中逆党如此猖獗,我们怎能坐视不理?”李景隆眼睛都红了,“难道要眼睁睁看著陛下与太子被人欺负?”
徐辉祖有些无奈地撇了撇嘴:“若是陛下不想退让,谁又能逼他?
是陛下立己不想掀起纷爭,如丑京中虽乱,但民间还算安稳。
只要太子殿下养好身体,陛下立然会重整旗鼓,大杀四方,你我静观其变即可。”
“可若是太子殿下...情况不好呢?”
李景隆的声音有些微妙。
徐辉祖眼神变得空洞,望著天空中的微风与浓密乌云,淡淡道:“那就更该大杀四方了——.”
李景隆瞳孔骤然收缩,瞬间明白了一件事,如丑桎梏陛下脚步的,唯有太子的身体。
若太子真有不测,陛下便再无任何牵绊。
到那时,不论好坏,但凡有所怀疑,尽可一概诛杀,民间立会拍手叫好。
就在这时,急促的脚步声立宫道尽头传来。
大太监李公公步履匆匆,看到站在墙角的徐辉祖与李景隆,面露急稍,连忙冲了过来:“魏国公、曹国公,陛下请二位即刻前往武英殿,说是有要事相商。”
大年初一,年关刚过,作为大明国都的应天城,本应喜气洋洋,此刻却被一股凝固氛围笼罩。
朝堂与民间皆是如此,就连走在街上的百姓都多了几分忧心忡忡,说话不敢大声,生怕被巡逻禁军盯上。
相较於以往,禁军比年前多了数倍不止,四方城门更是封锁得严严实实,但凡有半点身份瑕疵,就休想出城,甚至会被扣押审问。
一切的缘由,百姓们心知肚明,昨日皇城方向升起的黑色烟柱,人人都看在眼里。
谁都知道,祭天之时,皇宫附近失了火。
这等开年即至的不祥之兆,让所有人噤若寒蝉,不敢多提,更说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不仅民间百姓茫然,朝中诸位大臣也同样不明所以。
他们只知道火是莫名其妙燃起的,不仅都督府著了火,浦子口城也未能倖免。
这两处皆是应天最重要的军事重地,甚至堪称天下武將嚮往之地,如今两地同时失火,还偏偏选在祭天之时,容不得人不多想。
是武將有反心?还是有人见不得武將好?
临近上午,皇城內的气氛依旧压抑,中军都督府门前,徐辉祖身著甲冑,手握长刀,脸色凝重地望著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杂物房。
一旁的曹国公李景隆亦是如此。
微风轻拂,带著几分冷冽与萧瑟,空气中的焦湖味似乎更重了些。
李景隆看著前方残垣断壁中忙碌整理的都督府吏员,嘴角勾起一抹讥讽,淡淡道:“刚回京就见到这一幕,真是热闹。”
徐辉祖深吸一口气,又重重吐出,诧异地看了一眼李景隆。
相较於两年前,九江显然成熟了许多,一举一动都透著大人风范,不再是往日的毛躁模样。
“现在知道京中局势了吧?
祭天这等大日子,都有人敢捣乱,真是胆大包天。”
李景隆神色微妙,轻声发问:“查到什么了吗?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,神情愈发微妙:“什么都没有查到,似乎逆党只是为了放火,给朝廷一个下马威,或者说,给陛下一个下马威。”
李景隆眉头紧皱,这一日他已听闻关於太子的诸多內情,轻声道:“太子莫名其妙中毒,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下马威?”
徐辉祖听出了他话中的深意,反问道:“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?”
李景隆在中军都督府门前渡了两步,又看向不远处的左军都督府,面露思索:“行军打仗,讲究一石二鸟,甚至一石三鸟,如今逆党这般行事,或许不只是为了破坏祭天,说不定还有別的目的。
说到这里,他抬头追问:“烧毁了什么东西?或许能从烧毁的物件中能察觉到些许端倪。”
徐辉祖闻言,面露讚嘆,忍不住点了点头:“九江,你真的长大了。”
李景隆脸色一黑,没有说话,只是用眼神催促他继续。
徐辉祖笑了笑,缓缓道:“中军都督府烧了杂物房,里面放著一些废弃的文书,左军都督府烧毁了从洪武十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一应军事调动,以及受封將领的人员名单。
浦子口城也被烧毁了小半个案牘库,同样是军事调动、人员名单以及粮草辐重的运输路线,对了,还有朝廷在各处官道旁设立的储粮点位置。
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推测,逆党是想烧毁这些军事文书,以此掩盖边军吃空餉、肆意挪用粮仓粮食的事实。”
李景隆听后眉头一皱,思索片刻道:“我在西北这两年,虽也见过吃空餉、掏空粮仓之事,但都是极少数,若是仅仅为了这些,逆党就要烧毁整个案牘库,那边军得有多少粮仓被掏空?又有多少人吃空餉?
我想,若非达到半数之多,没人会冒这般风险。”
徐辉祖点头附和: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诸位侯爷也觉得此事不合常理,但除此之外,实在没有別的解释。”
“锦衣卫怎么说?”李景隆反问,“事情都发生快一日了,锦衣卫难道还没查到端倪?”
徐辉祖脸色有些古怪,眼神中甚至带著一丝讥讽,轻轻摇了摇头:“锦衣卫现在自顾不暇。”
“为何?”
“锦衣卫的秘狱也著火了,同样烧毁了储存的军事文书。”
“什么?”
李景隆惊呼出声,眼睛猛地瞪大,连忙追问:“是城北那个秘狱?那里也有文书备份?”
徐辉祖诧异地看了他一眼:“这你都知道?”
李景隆脸色一黑:“应天城是我爹主持重建的,我怎么会不知道?”
徐辉祖忽然笑了起来,点头道:“也是,就是你说的那个秘狱,那里当初是检校秘密关押犯人的地方,现在被锦衣卫接管,不少绝密文书都藏在里面,甚至还有一个大牢,靖寧侯就关在那。”
此话一出,李景隆脸色凝重到了极点。
他比谁都清楚应天城的弯弯绕绕,锦衣卫秘狱的位置,除了锦衣卫內部,整个应天城的权贵中知晓者屈指可数,皆是位高权重之辈。
如今秘狱的文书都被烧了,这背后是谁?又为了什么?
想到这里,李景隆压低声音,仅让两人听见:“会不会是逆党想要作乱,藉此烧毁人员密档,好將自己的人瞒下来?以后谋逆?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:“知道秘狱位置的人就那么多,有胆子在祭天之日三处同时动手的,也就那么几位。
对他们而言,亲信下属遍布大明,根本无须隱瞒,就算要瞒,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”
李景隆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三道人影,凉国公蓝玉、宋国公冯胜、颖国公傅友德。
军中能有这般胆子与能力,同时在三处动手的,或许只有这三人,他又看了看自己,再看了看徐辉祖,若是他们的父亲还在世,也能轻鬆做到,但他们如今还没有这般实力。
“这么说来,此事是查不出结果了?”
徐辉祖耸了耸肩,嘆了口气,无奈点头:“既然人家敢做,就不怕被查,再说了,就算查到了又如何?”
李景隆一愣,很快便反应过来。
如今这等局势,三司巴不得什么都查不出来。
若是真查出哪位国公想要谋反,事情只会更加复杂,局势將变得烈火烹油。
但他转念一想,又觉得不能不查:“就算现在不挑破,也得把幕后真凶查出来,日后再做清算,有调查方向吗?”
徐辉祖神情有些微妙,轻轻点头:“今早毛驤递上来一封文书,上面列出了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各类战事的主要將领。
我仔细看了看,死的死,病的病,还有一些背负谋反骂名,剩下的已经没几个了。”
“还有谁?”
李景隆眼睛眯了起来。
“凉国公、宋国公、颖国公、开国公、西平侯、全寧侯、定远侯、长兴侯、武定侯、
怀远侯,以及俞通渊和陆云逸。”
徐辉祖的声音越来越轻,像是提及了什么禁忌之事。
李景隆越听,脸色越是凝重,反问道:“只有这些?不是还有其他將领吗?耿忠、冯诚、寧正不也都活得好好的。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:“这是锦衣卫筛选出的名单,毛驤认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些。
当然,冯诚也有这个本事,但他远在云南,从不掺和朝廷之事,所以不在此列。”
李景隆脸色顿时变得古怪:“那云逸也不在京城啊。”
徐辉祖眼睛眯了起来,淡淡道:“按照毛驤的说法,他虽人不在京城,但应天商行、建筑商行、水泥商行都在。
这等垄断京畿商脉的庞然大物,无数人从中获利,他想要串联一些人,再容易不过。
甚至在毛驤给出的名单中,除了最前面几位国公侯爷,就是他了。”
“妈的,这毛驤果然不是个好东西!”
李景隆破口大骂,“他这是公报私仇!”
作为曹国公,他知晓毛驤能官復原职,全靠云逸向太子进言。
如今这把刀非但不砍向別人,反而对准了自己人,实在荒谬!
徐辉祖面露无奈:“锦衣卫的推测也並非毫无道理。”
“他们推测了什么?”
徐辉祖拉著李景隆离开中军都督府衙门口,走到稍远些的城墙根下,轻声道:“毛驤猜测,这是凉国公在对陛下表示不满,凉国公是幕后主使,真正动手的人是陆云逸。”
李景隆瞳孔骤然收缩:“胡言乱语,空口无凭!他为何这般说?”
“陛下对於京中逆党一退再退,太子殿下的病情也不见好转。”徐辉祖解释道,“凉国公已经几次在朝会上破口大骂茹等人,说他们是谋害太子的逆党,请陛下惩处,但陛下始终没有行动,凉国公才会以此表示不满。”
此话一出,李景隆眉头皱得更紧,眼中闪过一丝荒谬:“这毛驤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?
凉国公若是痛恨谋害太子的逆党,为何不直接对那些人下手,反而要对陛下表示不满?”
徐辉祖忽然笑了起来,伸手揉了揉眉心,面露愁容:“你怎么知道他没动手?
你刚回京,有些事情还没来得及知晓。
最近这些日子,京城的夜里可不太平,茹等权贵的府邸常常有歹人作祟,要么是流窜多年的盗匪,要么是通缉已久的流寇。
他们总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京城,潜入这些大人物的府邸。
若非府邸防卫森严,锦衣卫也出手相助,这些人早就死了。
听答儿麻说,锦衣卫在各个府邸的暗线已经暴露了不下百人,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贵。”
“这...还有这种事?”
李景隆拳头猛地紧握,呼吸急促起来。
京中的斗爭比他想像得还要可怕,竟然已经到了直接杀人的地步。
这在大明朝立国二十多年来,也只发生过寥寥数次。
徐辉祖继续道:“军中也有异动,西城门守將莫名其妙被替换,其部下五百人被调回浦子口城。
新调来的千户王子文,表面上与凉国公毫无关联,但调令是后军都督府事陈然所发,他十年前曾与凉国公一同出征西番,担任前锋。”
李景隆只觉得嘴唇莫名乾涩,反问:“这是要谋反?”
他又想了想,问道:“朝廷已经认定此事是凉国公和陆云逸所为?”
看到他的表情,徐辉祖挥了挥手,勉强挤出一丝笑容:“锦衣卫只是推测,丕无实据,毛驤与答儿麻也不敢乱说,是我逼问,他们才透露的。
与凉国公有著同样嫌疑的,还有宋国公与潁国公,他们都与驻外藩王有姻亲关係。
若是太子真有不测,他们未必没有取而代之的心思。”
此话一出,李景隆浑身汗毛倒竖,连忙看向四周,低声喝道:“慎言!这里是皇城!”
徐辉祖显然也意识到不妥,悻悻然摆了摆手,有些疲惫地开口:“最近的事情太多,一时失言,虽然不能明说,但京中不少人已经有了夺储的心思。
有人押注皇子,有人押注两个小殿下,变之乱成一团。”
“就没有盼著太子好转的?”
“有,但盼著太子不好的人更多。”徐辉祖道,“太子在时,天下安定,没人敢生出歪心思。
可现在太子抱恙,就算是原蜡安稳乔日的人,心中也难免胡思乱想。
有些念头一旦升起,就再也收不回去了。”
李景隆忽然想起一事,浑身紧绷:“你昨天问我秦王...秦王怎么了?他也有竭储之心?”
“不清楚。”徐辉祖摇头,“但坊间已经有了一些流言蜚语,太子在秦王的封地遭遇纵火,如丑又久病不起,秦王身为老二,容不得人不多想。”
“这等流言,必然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!”
徐辉祖点了点头:“必然的,神宫监最近与市易司走得很近,正在严查这些流言,也抓了不少人。
他们都老实交代了,是受人指使,拿了银子帆播的,但具体是谁指使的,却查不出来。”
“市易司也查不出来?”李景隆有些诧异。
他业控著新马商行,仅凭这一家商行,就知晓许多京城权贵都不知道的秘闻。
而牵史百万人生计的应天商行,理应知道得更多。
“能查得到源头,但...”徐辉祖顿了顿,“幕后之人太过狠辣,每当有新流言冒出来,神烈山的乱坟岗上就会多几具尸体,想来都是最先传播流言的人。
神宫监每每查到这里,线索就戛然而止。”
李景隆站在墙根下,双手叉,看著前方忙碌的吏员与军卒。
眼前的景乌看兄安定,他却能感受到暗流涌动,让他坐立不安:“咱们能做什么?”
徐辉祖摇了摇头:“像你我这般勛贵后继,最好不要掺和这些事。
你我与国同休,只要不捲入纷爭,不论將来是谁登基,都少不了你我的富贵,我最怕你一时衝动做了傻事,切烧谨言慎行。”
“现在京中逆党如此猖獗,我们怎能坐视不理?”李景隆眼睛都红了,“难道要眼睁睁看著陛下与太子被人欺负?”
徐辉祖有些无奈地撇了撇嘴:“若是陛下不想退让,谁又能逼他?
是陛下立己不想掀起纷爭,如丑京中虽乱,但民间还算安稳。
只要太子殿下养好身体,陛下立然会重整旗鼓,大杀四方,你我静观其变即可。”
“可若是太子殿下...情况不好呢?”
李景隆的声音有些微妙。
徐辉祖眼神变得空洞,望著天空中的微风与浓密乌云,淡淡道:“那就更该大杀四方了——.”
李景隆瞳孔骤然收缩,瞬间明白了一件事,如丑桎梏陛下脚步的,唯有太子的身体。
若太子真有不测,陛下便再无任何牵绊。
到那时,不论好坏,但凡有所怀疑,尽可一概诛杀,民间立会拍手叫好。
就在这时,急促的脚步声立宫道尽头传来。
大太监李公公步履匆匆,看到站在墙角的徐辉祖与李景隆,面露急稍,连忙冲了过来:“魏国公、曹国公,陛下请二位即刻前往武英殿,说是有要事相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