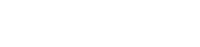“我看就是衝著老二来的,老二天天在外面赌博鬼混,得罪了不少人。这次看到老么你挣了钱,想用老二来要挟你。”大哥分析道。
“那怎么办啊?老二虽然混帐好赌,不爭气,但他是从我身上掉下的肉啊,罪不至死啊。老么,现在你有本事了,你能不能去救救他,把他救回来?”老妈恳求。
老爸蹲在门槛上,脸上的皱纹挤成一片,手抖得厉害,连菸袋锅子都拿不住。
老妈看著我,眼睛里满是哀求。估计她也不好意思,毕竟平常老二对我太刻薄。
大嫂低著头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不过我也知道大嫂对老二十分嫌弃。
看著一家老小惊慌失措的样子,我嘆了口气。
二哥的確是个混蛋,不是个东西,不仅想偷我的钱,还想害我,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寧。
但正如老妈所说的,血浓於水。
更关键的是,他罪不至死。
他要是死了,爹妈肯定会伤心。看在爹妈的份上,我得救他。
“你们別著急,我现在就去救他。”
“啊?怎么救啊?”老妈问。
“对方在这封信上说得清楚,让我去换人,我去了就行了,二哥就能回来。”
“那你不是很危险?我跟你一起去!”大哥说。
“不用,我一个人去。你们在家里把门关好,把大黑喊过来,多餵点它吃的,让它保持战斗力。我担心对面有调虎离山之计,我过去之后,他们来偷家。”我朝大黑狗吹了个口哨,招了招手,大黑狗跑了过来。
我咬破指尖,在空中以鲜血画符,然后一道符拍在它的狗脑门上。
大黑的眼神瞬间变得凶恶了不少。
我对狗说:“看著家,不让別人过来。”
为了万无一失,我还请了一个帮手。
家门口就是长江。
我走到江边上,伸手泡进长江里。
这长江和那回龙湾的浅水滩是连在一起的,心念所至,我感觉到了那个红衣新娘。
“红玉姑娘,请你过来一趟,帮我看著我家。如果有人想对我家人不轨,那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吸吸他们的阳气,补补身子。”
此时江面之下出现了一袭红色的嫁衣。
老爸老妈、大哥大嫂嚇了一跳。
我解释说:“这是红棺材里面的新娘,她不会主动现身。你们不招惹她,她就不会招惹你们。”
我正要出发的时候,赵癩子带人过来了。
难道他也要来趁火打劫?
没想到赵癩子是来帮忙的。
“江拐子,我听到有人踢你们家的狗,谁呀?我弄死他!”
这个人还真是言而有信,说以后认我当大哥,那就真认我当大哥。
我说:“可能是我家二哥的债主找过来討债了,你帮我看著家,不让別人进来。”
大嫂小声说:“我怕赵赖子进来。”
赵癩子尷尬笑两声说:“放心吧,我就蹲在门口。”
此时天快亮了,但还没有亮,正是最黑的时候。
我走进了黑暗之中。
所谓的乱葬岗,就是附近的一片野坟地,荒芜阴森。
那个地方白天都没多少人,晚上更是狗都不愿意往里面钻。今晚月亮被乌云遮住了,四周黑黢黢的。
很快就走到了乱葬岗。
那里有一片树林,我走进去,看到一棵歪脖子柳树。
树上掛著一盏灯笼,惨白惨白的,在风中摇晃。
借著灯笼的光影,我看见了一个人,二哥江滨。
他被一根麻绳绑著,双手高高吊起,脚尖勉勉强强能点一下地面,整个人都在颤抖,跟筛糠一样。
我往前走了几步,发现他狼狈不堪,一张脸已经被打肿了,身上都是泥土和鲜血,裤襠也湿了,显然是被嚇尿了。
“老么!救我!救我啊!”
二哥看到我,一下子眼睛瞪大了,拼命地挣扎哭喊。
而树下有一个坟包,坟包旁边站著几个人影。
他们流里流气的,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
我走过去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
那几个流里流气的人说: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哥哥欠了我们的债,弟弟来还,那也是正常。少废话,赶紧拿钱!”
隨著二哥断断续续的哭诉,和这几个人的嘲讽辱骂,我总算是把晚上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了。
原来二哥跟我大吵一架之后出了门,他还是趁我不注意,找老妈要了几百块钱跑出去赌博。一下子就输了个精光。
输光了的人都想翻本,他手上没钱,就找赌场的人借了高利贷。
二哥输红了眼,欠的钱越来越多,最后还不上,被人按在赌桌上。
赌场的老板拿出一把砍刀要剁掉他的手指抵债。
二哥一下子就怂了,嚇破了胆,跪在地上磕头求饶。
赌场的老板蹲在二哥面前,拍著他的脸说:“钱我可以不要,只要你做一件事,这些帐不仅可以一笔勾销,还能再赏你一笔钱。”
这件事就是回家剪我的头髮,或者拿我擦过汗的毛巾。
一开始二哥还有点犹豫,虽然他为人混蛋,但也知道我是他亲弟弟,而且拿这种贴身之物给外人,一看就邪乎,肯定是要害人的。
看著他犹豫,赌场老板翻了脸,恶狠狠地威胁道:“不干是吧?来人!现在就把他手指头砍下来!欠了多少钱?一万块。一千块一根指头,欠多少就砍多少根!”
二哥欠了一万块,十根指头都要被砍掉。
这时有一个客人跑过来唱红脸,哄骗二哥说:“江家老二,你想想,你弟弟是个傻子,傻了十年,你家养他养了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?看病又花了多少钱?那就是个拖累!以后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,这些钱本来都是你的。不如你就听老板的话,把东西拿了就行了,债也平了,剩下的钱你自己好好花,多好啊。那傻子死活不关你的事,你就拿点东西……”
在威逼利诱之下,二哥动摇了,於是他就回家偷我的毛巾。
没想到他的毛巾被我调包了,他拿著沾著鸡血的毛巾来交差。
而他交差的人,正穿著一双黑布鞋。
此时我看到了一双黑布鞋。黑布鞋的主人坐在坟包上,是一个乾瘦的老头,听附近的人称呼他为“阴鱼爷”。
不过此时这位阴鱼爷看起来比我吊在树上的二哥还要惨。
他的脸像是被火药崩过一样,头髮也被烧焦了,脸上还有几道炸伤的血痕,往外面渗著血,看起来狰狞可怖。
可以想像,他拿著我的毛巾做法术,以为上面沾著我的气息,没想到上面沾著至阳的黑鸡血。他修炼的是阴损邪术,水火不容,而且毫无准备,法坛当场就炸了。他不仅没有害到我,自己还被炸得七荤八素。
当著这么多徒弟的面丟了这么大的脸,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於是他把我二哥扣下,打了一顿,逼我过来。
“嘿嘿,小子,你来了。”
我看著这个穿著黑布鞋的老头,想起老爸肩膀上的两道青印子,不由得捏紧了拳头。
“那怎么办啊?老二虽然混帐好赌,不爭气,但他是从我身上掉下的肉啊,罪不至死啊。老么,现在你有本事了,你能不能去救救他,把他救回来?”老妈恳求。
老爸蹲在门槛上,脸上的皱纹挤成一片,手抖得厉害,连菸袋锅子都拿不住。
老妈看著我,眼睛里满是哀求。估计她也不好意思,毕竟平常老二对我太刻薄。
大嫂低著头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不过我也知道大嫂对老二十分嫌弃。
看著一家老小惊慌失措的样子,我嘆了口气。
二哥的確是个混蛋,不是个东西,不仅想偷我的钱,还想害我,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寧。
但正如老妈所说的,血浓於水。
更关键的是,他罪不至死。
他要是死了,爹妈肯定会伤心。看在爹妈的份上,我得救他。
“你们別著急,我现在就去救他。”
“啊?怎么救啊?”老妈问。
“对方在这封信上说得清楚,让我去换人,我去了就行了,二哥就能回来。”
“那你不是很危险?我跟你一起去!”大哥说。
“不用,我一个人去。你们在家里把门关好,把大黑喊过来,多餵点它吃的,让它保持战斗力。我担心对面有调虎离山之计,我过去之后,他们来偷家。”我朝大黑狗吹了个口哨,招了招手,大黑狗跑了过来。
我咬破指尖,在空中以鲜血画符,然后一道符拍在它的狗脑门上。
大黑的眼神瞬间变得凶恶了不少。
我对狗说:“看著家,不让別人过来。”
为了万无一失,我还请了一个帮手。
家门口就是长江。
我走到江边上,伸手泡进长江里。
这长江和那回龙湾的浅水滩是连在一起的,心念所至,我感觉到了那个红衣新娘。
“红玉姑娘,请你过来一趟,帮我看著我家。如果有人想对我家人不轨,那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吸吸他们的阳气,补补身子。”
此时江面之下出现了一袭红色的嫁衣。
老爸老妈、大哥大嫂嚇了一跳。
我解释说:“这是红棺材里面的新娘,她不会主动现身。你们不招惹她,她就不会招惹你们。”
我正要出发的时候,赵癩子带人过来了。
难道他也要来趁火打劫?
没想到赵癩子是来帮忙的。
“江拐子,我听到有人踢你们家的狗,谁呀?我弄死他!”
这个人还真是言而有信,说以后认我当大哥,那就真认我当大哥。
我说:“可能是我家二哥的债主找过来討债了,你帮我看著家,不让別人进来。”
大嫂小声说:“我怕赵赖子进来。”
赵癩子尷尬笑两声说:“放心吧,我就蹲在门口。”
此时天快亮了,但还没有亮,正是最黑的时候。
我走进了黑暗之中。
所谓的乱葬岗,就是附近的一片野坟地,荒芜阴森。
那个地方白天都没多少人,晚上更是狗都不愿意往里面钻。今晚月亮被乌云遮住了,四周黑黢黢的。
很快就走到了乱葬岗。
那里有一片树林,我走进去,看到一棵歪脖子柳树。
树上掛著一盏灯笼,惨白惨白的,在风中摇晃。
借著灯笼的光影,我看见了一个人,二哥江滨。
他被一根麻绳绑著,双手高高吊起,脚尖勉勉强强能点一下地面,整个人都在颤抖,跟筛糠一样。
我往前走了几步,发现他狼狈不堪,一张脸已经被打肿了,身上都是泥土和鲜血,裤襠也湿了,显然是被嚇尿了。
“老么!救我!救我啊!”
二哥看到我,一下子眼睛瞪大了,拼命地挣扎哭喊。
而树下有一个坟包,坟包旁边站著几个人影。
他们流里流气的,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
我走过去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
那几个流里流气的人说: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哥哥欠了我们的债,弟弟来还,那也是正常。少废话,赶紧拿钱!”
隨著二哥断断续续的哭诉,和这几个人的嘲讽辱骂,我总算是把晚上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了。
原来二哥跟我大吵一架之后出了门,他还是趁我不注意,找老妈要了几百块钱跑出去赌博。一下子就输了个精光。
输光了的人都想翻本,他手上没钱,就找赌场的人借了高利贷。
二哥输红了眼,欠的钱越来越多,最后还不上,被人按在赌桌上。
赌场的老板拿出一把砍刀要剁掉他的手指抵债。
二哥一下子就怂了,嚇破了胆,跪在地上磕头求饶。
赌场的老板蹲在二哥面前,拍著他的脸说:“钱我可以不要,只要你做一件事,这些帐不仅可以一笔勾销,还能再赏你一笔钱。”
这件事就是回家剪我的头髮,或者拿我擦过汗的毛巾。
一开始二哥还有点犹豫,虽然他为人混蛋,但也知道我是他亲弟弟,而且拿这种贴身之物给外人,一看就邪乎,肯定是要害人的。
看著他犹豫,赌场老板翻了脸,恶狠狠地威胁道:“不干是吧?来人!现在就把他手指头砍下来!欠了多少钱?一万块。一千块一根指头,欠多少就砍多少根!”
二哥欠了一万块,十根指头都要被砍掉。
这时有一个客人跑过来唱红脸,哄骗二哥说:“江家老二,你想想,你弟弟是个傻子,傻了十年,你家养他养了这么多年花了多少钱?看病又花了多少钱?那就是个拖累!以后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,这些钱本来都是你的。不如你就听老板的话,把东西拿了就行了,债也平了,剩下的钱你自己好好花,多好啊。那傻子死活不关你的事,你就拿点东西……”
在威逼利诱之下,二哥动摇了,於是他就回家偷我的毛巾。
没想到他的毛巾被我调包了,他拿著沾著鸡血的毛巾来交差。
而他交差的人,正穿著一双黑布鞋。
此时我看到了一双黑布鞋。黑布鞋的主人坐在坟包上,是一个乾瘦的老头,听附近的人称呼他为“阴鱼爷”。
不过此时这位阴鱼爷看起来比我吊在树上的二哥还要惨。
他的脸像是被火药崩过一样,头髮也被烧焦了,脸上还有几道炸伤的血痕,往外面渗著血,看起来狰狞可怖。
可以想像,他拿著我的毛巾做法术,以为上面沾著我的气息,没想到上面沾著至阳的黑鸡血。他修炼的是阴损邪术,水火不容,而且毫无准备,法坛当场就炸了。他不仅没有害到我,自己还被炸得七荤八素。
当著这么多徒弟的面丟了这么大的脸,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於是他把我二哥扣下,打了一顿,逼我过来。
“嘿嘿,小子,你来了。”
我看著这个穿著黑布鞋的老头,想起老爸肩膀上的两道青印子,不由得捏紧了拳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