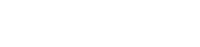“就像方才他一进门便对你拳打脚踢一样,在他心中从来就没把你当成他的嫡亲骨肉。”
魏顏之浑身一颤,彻底沉默了下来。
旁边的魏邱闻言,脸上的暴怒也是一滯。
回想起自己刚才进门之后的举动。
他张了张嘴,也沉默了。
铜豌豆却是步步紧逼,再次拋出了刚才那个问题。
“那么现在,你如何看待魏基之承认私通后,仅仅被打断腿这件事?”
“你又在纠缠这个问题!”
魏顏之闻言就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,猛地抬起头,大声怒吼。
铜豌豆神色从容,语气篤定地说道。
“若我是你,在得知魏柔怀了我的骨肉后,必定惊恐万分,因为一旦此事被宋国公察觉是我所为,他定会取我性命。”
“因此,我必须设法嫁祸给魏基之。”
“毕竟国公爷对他疼爱有加,让他来代替我承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“你不要信口雌黄,说话要负责任的。”
魏顏之被戳破了心思,顿时面色涨红的反驳。
“此时此刻,睿王殿下、国公爷、府尹大人皆在此处,我当然会对我的问话负责。”
铜豌豆上前一步,轻轻摇了摇头。
目光中满是怜悯的望著魏顏之。
“魏基之是嫡子,生来便享尽尊荣,集万千宠爱於一身。”
“而你不过是个无人疼惜的庶子。”
“你恨魏基之,恨他夺走了本可属於你的一切,所以你恨不得杀了他,恨不得让整个魏府为你所受的冷遇付出代价。”
“不是的,我根本不恨魏基之,我们兄弟感情一向深厚!”
魏顏之不断的嘶声大吼。
“不过我来告诉你,你骨子里就是个懦夫,你根本没胆量真刀真枪地报復魏家。”
“所以你才用花言巧语诱骗了魏柔,通过和她私通这种齷齪手段,来满足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。”
“来暗中报復魏家对你的不公。”
“你胡说,我没有和魏柔私通。”
魏顏之顿时脸色惨白,他厉声反驳道。
“可魏柔却当真爱上了你,她甚至想和你远走高飞,而你却捨不得眼前的荣华富贵。”
“你绞尽脑汁稳住她,可她在送亲路上还三番两次冒险找你私会,即便到了朔州城外,她仍在逼你表態。”
“她指著鼻子骂你。”
说到这里,铜豌豆指著魏顏之的鼻子骂道。
“她骂你是个懦夫,是废物,敢做不敢当,只会嫁祸给兄长,让別人背锅。”
铜豌豆的声音陡然拔高。
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魏顏之的心上。
“骂你眼睁睁看著自己的亲骨肉被强行墮掉,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”
“这世上,再找不出比你更窝囊、更没种的软蛋。”
“你胡说,她根本没有这样骂过我。”
魏顏之见铜豌豆竟將自己內心最不堪的懦弱彻底撕开,整个人已慌得六神无主。
下意识地脱口反驳道。
“那你为什么要用剑从她的后脑插进去?”
铜豌豆顿时便抓住他心神大乱的瞬间。
骤然发问。
“那是因为我担心她说出实情坏了我的前程,才用剑…”
魏顏之慌乱之下,脱口而出。
可话刚说了一半,他猛地意识到失言。
脸色唰地惨白如纸,慌忙抬手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魏顏之这句脱口而出的实情,就如同一道惊雷,狠狠的炸响在厅堂之中。
剎那间,满堂皆寂,落针可闻。
所有人的目光,全都齐刷刷地钉在了魏顏之惨白的脸上。
睿王萧启瞳孔猛的一缩,死死的握住了拳头。
他知道这意味著什么。
萧迟更是倒吸一口凉气,眼中全都是难以置信的骇然。
他也明白,自己真的错怪了魏基之。
魏基之的死他难逃罪责。
宋国公魏邱更是浑身剧震,鬚髮皆张。
死死盯著这个恨透了自己的好儿子。
府尹也张大了嘴巴。
他知道,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。
要是一般的冤假错案,自己还能想办法捂过去。
可现在事情涉及到当朝国公。
他无论如何躲不过去。
这一刻,真相已经血淋淋地剖开在来所有人面前。
魏顏之虽已面无人色,却仍然色厉內荏地高声喊道。
“你…你这是诱供!”
“你根本没有证据,全是故意引导我说的。”
“根本没这回事,大家不要被他骗了。”
“你要证据?”
一旁的瓦罐鸡闻言呵呵一笑,眼中闪过一丝嘲讽。
“好,我给你证据。”
说罢,他再次抬手一挥。
身后一名锦衣卫应声上前,手中捧著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。
包袱外层还凝结著一层细密的白霜。
那锦衣卫小心翼翼地將包袱放在地上,缓缓展开。
隨著包袱被缓缓打开,一股刺骨的寒气瀰漫开来。
里面赫然是一颗人头。
虽然面容因冰冻而略显青白,但五官轮廓依然清晰可辨。
正是魏柔失踪的脑袋。
魏顏之嚇得差点魂飞魄散。
双腿一软,扑通一声瘫坐在地。
他双目圆睁,死死盯著那颗头颅,嘴里语无伦次的哆嗦著。
“不…不可能。”
“你明明…明明被那位高人施法变走了啊!”
“怎么会在这里?”
魏邱则踉蹌著扑上前去,当彻彻底底看清那颗脑袋的面容时,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。
“我的女儿啊!!”
萧迟怒视瓦罐鸡,厉声质问道。
“魏柔的尸首为何会落在你们锦衣卫手中?”
“是不是你们在暗中耍什么手段?”
“说来也巧。”
瓦罐鸡摊了摊手,神色坦然道。
“我手下一名緹骑前夜去榕树林小解时,无意中发现了这颗脑袋。”
“他当即断定必有冤情,便將其带回百户所,用冰仔细封存,以待日后查明真相。”
“谁曾想,这竟是魏家小姐的首级。”
他並没有过多在这件事上纠缠,说著话锋一转,指向地上那颗脑袋。
“诸位请看,魏柔是被人以长剑从后脑贯入而死,剑锋凌厉无比,穿透颅骨时竟无半分阻塞。”
“足见凶器绝非凡铁,定是出自高人之手的定製兵刃。”
“魏顏之,可否將你隨身佩剑取出?”
“让我与这伤口比对一番?”
魏顏之彻底没招了,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为。
魏顏之浑身一颤,彻底沉默了下来。
旁边的魏邱闻言,脸上的暴怒也是一滯。
回想起自己刚才进门之后的举动。
他张了张嘴,也沉默了。
铜豌豆却是步步紧逼,再次拋出了刚才那个问题。
“那么现在,你如何看待魏基之承认私通后,仅仅被打断腿这件事?”
“你又在纠缠这个问题!”
魏顏之闻言就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,猛地抬起头,大声怒吼。
铜豌豆神色从容,语气篤定地说道。
“若我是你,在得知魏柔怀了我的骨肉后,必定惊恐万分,因为一旦此事被宋国公察觉是我所为,他定会取我性命。”
“因此,我必须设法嫁祸给魏基之。”
“毕竟国公爷对他疼爱有加,让他来代替我承担才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“你不要信口雌黄,说话要负责任的。”
魏顏之被戳破了心思,顿时面色涨红的反驳。
“此时此刻,睿王殿下、国公爷、府尹大人皆在此处,我当然会对我的问话负责。”
铜豌豆上前一步,轻轻摇了摇头。
目光中满是怜悯的望著魏顏之。
“魏基之是嫡子,生来便享尽尊荣,集万千宠爱於一身。”
“而你不过是个无人疼惜的庶子。”
“你恨魏基之,恨他夺走了本可属於你的一切,所以你恨不得杀了他,恨不得让整个魏府为你所受的冷遇付出代价。”
“不是的,我根本不恨魏基之,我们兄弟感情一向深厚!”
魏顏之不断的嘶声大吼。
“不过我来告诉你,你骨子里就是个懦夫,你根本没胆量真刀真枪地报復魏家。”
“所以你才用花言巧语诱骗了魏柔,通过和她私通这种齷齪手段,来满足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。”
“来暗中报復魏家对你的不公。”
“你胡说,我没有和魏柔私通。”
魏顏之顿时脸色惨白,他厉声反驳道。
“可魏柔却当真爱上了你,她甚至想和你远走高飞,而你却捨不得眼前的荣华富贵。”
“你绞尽脑汁稳住她,可她在送亲路上还三番两次冒险找你私会,即便到了朔州城外,她仍在逼你表態。”
“她指著鼻子骂你。”
说到这里,铜豌豆指著魏顏之的鼻子骂道。
“她骂你是个懦夫,是废物,敢做不敢当,只会嫁祸给兄长,让別人背锅。”
铜豌豆的声音陡然拔高。
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魏顏之的心上。
“骂你眼睁睁看著自己的亲骨肉被强行墮掉,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”
“这世上,再找不出比你更窝囊、更没种的软蛋。”
“你胡说,她根本没有这样骂过我。”
魏顏之见铜豌豆竟將自己內心最不堪的懦弱彻底撕开,整个人已慌得六神无主。
下意识地脱口反驳道。
“那你为什么要用剑从她的后脑插进去?”
铜豌豆顿时便抓住他心神大乱的瞬间。
骤然发问。
“那是因为我担心她说出实情坏了我的前程,才用剑…”
魏顏之慌乱之下,脱口而出。
可话刚说了一半,他猛地意识到失言。
脸色唰地惨白如纸,慌忙抬手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魏顏之这句脱口而出的实情,就如同一道惊雷,狠狠的炸响在厅堂之中。
剎那间,满堂皆寂,落针可闻。
所有人的目光,全都齐刷刷地钉在了魏顏之惨白的脸上。
睿王萧启瞳孔猛的一缩,死死的握住了拳头。
他知道这意味著什么。
萧迟更是倒吸一口凉气,眼中全都是难以置信的骇然。
他也明白,自己真的错怪了魏基之。
魏基之的死他难逃罪责。
宋国公魏邱更是浑身剧震,鬚髮皆张。
死死盯著这个恨透了自己的好儿子。
府尹也张大了嘴巴。
他知道,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。
要是一般的冤假错案,自己还能想办法捂过去。
可现在事情涉及到当朝国公。
他无论如何躲不过去。
这一刻,真相已经血淋淋地剖开在来所有人面前。
魏顏之虽已面无人色,却仍然色厉內荏地高声喊道。
“你…你这是诱供!”
“你根本没有证据,全是故意引导我说的。”
“根本没这回事,大家不要被他骗了。”
“你要证据?”
一旁的瓦罐鸡闻言呵呵一笑,眼中闪过一丝嘲讽。
“好,我给你证据。”
说罢,他再次抬手一挥。
身后一名锦衣卫应声上前,手中捧著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袱。
包袱外层还凝结著一层细密的白霜。
那锦衣卫小心翼翼地將包袱放在地上,缓缓展开。
隨著包袱被缓缓打开,一股刺骨的寒气瀰漫开来。
里面赫然是一颗人头。
虽然面容因冰冻而略显青白,但五官轮廓依然清晰可辨。
正是魏柔失踪的脑袋。
魏顏之嚇得差点魂飞魄散。
双腿一软,扑通一声瘫坐在地。
他双目圆睁,死死盯著那颗头颅,嘴里语无伦次的哆嗦著。
“不…不可能。”
“你明明…明明被那位高人施法变走了啊!”
“怎么会在这里?”
魏邱则踉蹌著扑上前去,当彻彻底底看清那颗脑袋的面容时,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。
“我的女儿啊!!”
萧迟怒视瓦罐鸡,厉声质问道。
“魏柔的尸首为何会落在你们锦衣卫手中?”
“是不是你们在暗中耍什么手段?”
“说来也巧。”
瓦罐鸡摊了摊手,神色坦然道。
“我手下一名緹骑前夜去榕树林小解时,无意中发现了这颗脑袋。”
“他当即断定必有冤情,便將其带回百户所,用冰仔细封存,以待日后查明真相。”
“谁曾想,这竟是魏家小姐的首级。”
他並没有过多在这件事上纠缠,说著话锋一转,指向地上那颗脑袋。
“诸位请看,魏柔是被人以长剑从后脑贯入而死,剑锋凌厉无比,穿透颅骨时竟无半分阻塞。”
“足见凶器绝非凡铁,定是出自高人之手的定製兵刃。”
“魏顏之,可否將你隨身佩剑取出?”
“让我与这伤口比对一番?”
魏顏之彻底没招了,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