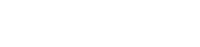侍立在一旁的东厂督主曹至淳闻言,那双平日里总是半眯著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厉色。
“主子爷圣明!”
“奴婢瞧著,这事儿也透著邪性。”
“这伙人分明是有组织、有预谋,串通好了来给主子爷您添堵,妄图胁迫天听。”
“奴婢这就让东厂的孩儿们动手,把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全都请到昭狱里去坐坐。”
“主子爷放心,到了奴婢那里,任他是铁打的骨头铜铸的嘴,奴婢也自有办法。”
“保准让他们把幕后是谁在兴风作浪,交代得一清二楚。”
朱厚聪闻言,看了看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奏摺,最终还是罢了罢手。
这股风潮来得如此迅猛、集中,他也知道背后显然有人精心策划。
群臣此举不仅关乎皇位继承,更隱隱包含著对他这位不安分帝王的冒险风格不满。
诚然,里面確实有人心怀不轨,但也有人確实是公忠体国。
一桿子打死所有人的做法不可行。
想到这里,朱厚聪眼中寒芒一闪而过。
他现在有一种想把罪魁祸首萧景亭弄死的想法。
这些奏摺一个个说得冠冕堂皇,其实个中意思再明显不过。
那就是立裕王萧景亭为储。
论嫡论长,除了他萧景亭最有资格当太子,还能有谁?
而且他已经从朱七那里证实过了。
果然是他的好儿子不甘寂寞,在背后推波助澜。
如果不能解决问题,那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。
朱厚聪在心里不断权衡著。
此时若直接杀了萧景亭,固然能解一时之气,但后患无穷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,裕王萧景亭刚被眾人推出来便立刻暴毙,天下人会如何想?
满朝文武会如何想?
他们不会相信什么意外或疾病,十有八九都会认定,是自己这个皇帝容不下儿子。
暗中安排人动的手。
想到这里,朱厚聪的目光变得更加幽深。
尤其是他如今已然返老还童,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寿元。
在世人的眼中,他想做万万年的皇帝,也並非没有可能。
一旦这个想法根植於人心,而萧景亭的死又万一留下了痕跡,被有心人利用…
即使没有痕跡,只要有人故意散播自己这个皇帝想永掌皇权,所以把继承人都杀死的谣言…
那么,引发的將是天下人的惶恐!
这种恐慌,会蔓延到他最亲近的人身上,比如萧雪鱼、晓梦她们。
因为她们会想,皇上能毫无缘由地把堂堂裕王说杀就杀,那他们的孩子呢?
將来还能有命在吗?
这份猜忌与恐惧,足以撕裂最牢固的信任。
毕竟他看起来確实还能活很多年。
歷史上皇帝杀对自己有威胁的皇子也並非稀有的事。
更重要的一点,即便眼下凭藉他的威望与实力,无人敢反,无人敢言。
但他的其他儿子们呢?
比如萧景恪、萧景熙他们…
他们得知兄长如此下场,又会作何感想?
当他们得出“父皇永远不想让位,並且会清除任何可能的继承人”这个结论后,他们岂能不自危?
岂能不恐慌?
到了那时,为了自保,他们或许也不会坐以待毙,而是会联合起来拼死反抗。
届时便是真的祸起萧墙。
而且一旦这种猜疑形成,有心人甚至会將之前景桓、景琰等人的死,也一併算到他这个皇帝的头上。
认为是他为了清除障碍而下的毒手。
届时他便是百口莫辩。
杀一子而失天下人心,此乃取乱之道,智者所不为也。
倒不如以退为进。
反正整个朝局都在他的掌控当中,萧景亭身边也还有朱七这个傀儡。
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。
自己则在背后安心布局,等北境安定之后,再想办法把裕王势力连根拔起。
“严嵩你去,宣裕王来覲见。”
“奴婢这就去。”
严嵩一愣,隨即连忙应下。
旁边的曹至淳也有些发愣,不是让他这个东厂嘟嘟去,而是让严嵩去。
別看只是二选一,这其中传达的意思可大有不同。
难道皇上有意立储?
即便是严嵩,也不敢过多猜测。
伴君如伴虎,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明白。
於是不动声色地將萧景亭召至万寿宫,任何暗示都没有给。
“儿臣参见父皇。”
萧景亭一踏入万寿宫,便依足礼数,恭敬地跪拜行礼。
姿態谦卑得倒像是个大孝子。
如果不是从朱七那里了解了实情,说不定还真叫这个孽障给哄住了。
“起来吧!”
朱厚聪说完一句,又吩咐严嵩。
“严嵩,给裕王搬个绣墩来。”
“儿臣多谢父皇恩典。”
萧景亭这才缓缓起身,小心翼翼地在严嵩拿来的绣墩上坐了半个屁股。
身体依旧微微前倾。
保持著一副聆听训示的姿態。
朱厚聪见状,脸上浮现出一抹追忆,连语气也变得温和了起来。
“景亭啊!”
“说起来,你在朕的诸多皇子之中,一直都是最得朕心、最受朕疼爱的一个。”
“朕每每看到你,就不由得想起当年为了治好你的腿疾,朕是如何派人四处寻访名医,搜罗奇药的。”
“那段往事,如今想来仍是记忆犹新。”
“你可还记得啊?”
然而这番话听在萧景亭耳中,却只觉得无比彆扭。
尤其是当他抬眼看向御座,映入眼帘的是父皇那张年轻得过分的面容时,他完全无法代入父子情深之中。
但他不敢有丝毫表露。
连忙低下头,用更加感激涕零的语气回应道。
“父皇天恩,儿臣岂敢忘却!”
“当年若非父皇倾力相救,儿臣此生恐怕都难以站立行走。”
“此恩山高海深,儿臣没齿难忘。”
他记得!
他当然记得!
当初那枚金丹多么神奇,顷刻之间便治好了他的腿疾。
可就是有著这么神奇的金丹,居然还让他的母后中毒而亡,这其中难道没有猫腻?
宽大的袍袖之下,萧景亭的拳头暗中猛地攥紧。
指甲深深嵌入掌心,带来一阵刺痛感。
可这刺痛,远不及他心中的痛恨。
他知道,自己母后的死,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。
就是眼前这个道貌岸然,看似关怀备至的男人一手安排的。
可他什么都做不了。
对面这个男人是君,自己是臣。
他掌握著生杀予夺的至高权柄,掌控著整个大明的力量。
而自己除了一个亲王的虚名,一无所有。
“主子爷圣明!”
“奴婢瞧著,这事儿也透著邪性。”
“这伙人分明是有组织、有预谋,串通好了来给主子爷您添堵,妄图胁迫天听。”
“奴婢这就让东厂的孩儿们动手,把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全都请到昭狱里去坐坐。”
“主子爷放心,到了奴婢那里,任他是铁打的骨头铜铸的嘴,奴婢也自有办法。”
“保准让他们把幕后是谁在兴风作浪,交代得一清二楚。”
朱厚聪闻言,看了看案头那堆积如山的奏摺,最终还是罢了罢手。
这股风潮来得如此迅猛、集中,他也知道背后显然有人精心策划。
群臣此举不仅关乎皇位继承,更隱隱包含著对他这位不安分帝王的冒险风格不满。
诚然,里面確实有人心怀不轨,但也有人確实是公忠体国。
一桿子打死所有人的做法不可行。
想到这里,朱厚聪眼中寒芒一闪而过。
他现在有一种想把罪魁祸首萧景亭弄死的想法。
这些奏摺一个个说得冠冕堂皇,其实个中意思再明显不过。
那就是立裕王萧景亭为储。
论嫡论长,除了他萧景亭最有资格当太子,还能有谁?
而且他已经从朱七那里证实过了。
果然是他的好儿子不甘寂寞,在背后推波助澜。
如果不能解决问题,那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,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。
朱厚聪在心里不断权衡著。
此时若直接杀了萧景亭,固然能解一时之气,但后患无穷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,裕王萧景亭刚被眾人推出来便立刻暴毙,天下人会如何想?
满朝文武会如何想?
他们不会相信什么意外或疾病,十有八九都会认定,是自己这个皇帝容不下儿子。
暗中安排人动的手。
想到这里,朱厚聪的目光变得更加幽深。
尤其是他如今已然返老还童,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寿元。
在世人的眼中,他想做万万年的皇帝,也並非没有可能。
一旦这个想法根植於人心,而萧景亭的死又万一留下了痕跡,被有心人利用…
即使没有痕跡,只要有人故意散播自己这个皇帝想永掌皇权,所以把继承人都杀死的谣言…
那么,引发的將是天下人的惶恐!
这种恐慌,会蔓延到他最亲近的人身上,比如萧雪鱼、晓梦她们。
因为她们会想,皇上能毫无缘由地把堂堂裕王说杀就杀,那他们的孩子呢?
將来还能有命在吗?
这份猜忌与恐惧,足以撕裂最牢固的信任。
毕竟他看起来確实还能活很多年。
歷史上皇帝杀对自己有威胁的皇子也並非稀有的事。
更重要的一点,即便眼下凭藉他的威望与实力,无人敢反,无人敢言。
但他的其他儿子们呢?
比如萧景恪、萧景熙他们…
他们得知兄长如此下场,又会作何感想?
当他们得出“父皇永远不想让位,並且会清除任何可能的继承人”这个结论后,他们岂能不自危?
岂能不恐慌?
到了那时,为了自保,他们或许也不会坐以待毙,而是会联合起来拼死反抗。
届时便是真的祸起萧墙。
而且一旦这种猜疑形成,有心人甚至会將之前景桓、景琰等人的死,也一併算到他这个皇帝的头上。
认为是他为了清除障碍而下的毒手。
届时他便是百口莫辩。
杀一子而失天下人心,此乃取乱之道,智者所不为也。
倒不如以退为进。
反正整个朝局都在他的掌控当中,萧景亭身边也还有朱七这个傀儡。
谅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。
自己则在背后安心布局,等北境安定之后,再想办法把裕王势力连根拔起。
“严嵩你去,宣裕王来覲见。”
“奴婢这就去。”
严嵩一愣,隨即连忙应下。
旁边的曹至淳也有些发愣,不是让他这个东厂嘟嘟去,而是让严嵩去。
別看只是二选一,这其中传达的意思可大有不同。
难道皇上有意立储?
即便是严嵩,也不敢过多猜测。
伴君如伴虎,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明白。
於是不动声色地將萧景亭召至万寿宫,任何暗示都没有给。
“儿臣参见父皇。”
萧景亭一踏入万寿宫,便依足礼数,恭敬地跪拜行礼。
姿態谦卑得倒像是个大孝子。
如果不是从朱七那里了解了实情,说不定还真叫这个孽障给哄住了。
“起来吧!”
朱厚聪说完一句,又吩咐严嵩。
“严嵩,给裕王搬个绣墩来。”
“儿臣多谢父皇恩典。”
萧景亭这才缓缓起身,小心翼翼地在严嵩拿来的绣墩上坐了半个屁股。
身体依旧微微前倾。
保持著一副聆听训示的姿態。
朱厚聪见状,脸上浮现出一抹追忆,连语气也变得温和了起来。
“景亭啊!”
“说起来,你在朕的诸多皇子之中,一直都是最得朕心、最受朕疼爱的一个。”
“朕每每看到你,就不由得想起当年为了治好你的腿疾,朕是如何派人四处寻访名医,搜罗奇药的。”
“那段往事,如今想来仍是记忆犹新。”
“你可还记得啊?”
然而这番话听在萧景亭耳中,却只觉得无比彆扭。
尤其是当他抬眼看向御座,映入眼帘的是父皇那张年轻得过分的面容时,他完全无法代入父子情深之中。
但他不敢有丝毫表露。
连忙低下头,用更加感激涕零的语气回应道。
“父皇天恩,儿臣岂敢忘却!”
“当年若非父皇倾力相救,儿臣此生恐怕都难以站立行走。”
“此恩山高海深,儿臣没齿难忘。”
他记得!
他当然记得!
当初那枚金丹多么神奇,顷刻之间便治好了他的腿疾。
可就是有著这么神奇的金丹,居然还让他的母后中毒而亡,这其中难道没有猫腻?
宽大的袍袖之下,萧景亭的拳头暗中猛地攥紧。
指甲深深嵌入掌心,带来一阵刺痛感。
可这刺痛,远不及他心中的痛恨。
他知道,自己母后的死,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。
就是眼前这个道貌岸然,看似关怀备至的男人一手安排的。
可他什么都做不了。
对面这个男人是君,自己是臣。
他掌握著生杀予夺的至高权柄,掌控著整个大明的力量。
而自己除了一个亲王的虚名,一无所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