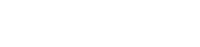齐敏一回到刑部衙门,便唤来了閆矛清,让他负责杨柳心杀人案。
反正閆矛清已经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,不如废物利用,先拿来顶一次锅。
可怜閆矛清还不知道自己被卖了。
听说是誉王特地嘱咐的,还以为能够同时攀上了誉王、齐敏和何敬中三个大人物。
京兆尹府才將何文新移送到刑部,他便屁顛屁顛的替其偽造证据。
说来也是巧。
閆矛清前脚才把何文新用罐子砸死邱泽的命案,硬生生改成了“邱泽酒后失足,不慎撞上罐子自尽“。
正得意自己的杰作,幻想著巴结上誉王从此一步登天。
后脚东厂的番子就闯进来了。
閆矛清抬头只见一队东厂番子鱼贯而入,为首的档头手持铁链,冷笑连连。
“閆矛清,涉嫌庆国公一案查抄时贪墨,抓起来。“
档头一声令下,几个番子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。
“誒!你们干什么。“
閆矛清被按在地上,还在拼命挣扎。
“凭什么抓我,我没有贪墨,我没有贪墨啊!“
档头冷笑一声,一脚踩在他背上。
“有没有贪墨,可不是你说了算的,带走!“
“等等!“
閆矛清突然扯著嗓子嚎叫。
“我上头有人,我上头有人!“
这话一出,只见那群东厂番子突然“噌噌噌“全部拔刀。
一个个跟猴子似的躥上了屋顶。
轰隆!
年久失修的屋顶哪经得起这番折腾。
整个房顶轰然塌陷,瓦片木樑劈头盖脸砸下来。
把閆矛清砸得头破血流。
“你个表…“
档头从废墟里爬出来,拍著身上的灰,气冲冲走到閆矛清面前。
“上头哪有人?”
“敢骗东厂,等死吧你!”
说著抬手就是两个响亮的大耳刮子,打得閆矛清眼冒金星。
“带走!“
他大手一挥,几个灰头土脸的番子从废墟里钻出来。
拖著彻底懵逼的閆矛清就往外走。
齐敏此刻正猫著腰躲在值房中,一只眼睛紧贴著窗缝看著外面。
看著閆矛清像条死狗似的被东厂拖走,他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上翘,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。
心里美得跟吃了蜜蜂屎似的。
这下子,何文新那小子也按誉王的意思放了。
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沾过案子,誉王和何敬之还得呈他的情。
最后,他还成功的让閆矛清那个蠢货把黑锅背得严严实实。
就算將来有人要翻旧帐,那也只能查到死人头上。
他可不认为,閆矛清进了詔狱,还能有机会活著走出来。
“我可真是个小天才。”
他舒舒服服的躺在太师椅上,美滋滋地唱起小曲来。
閆矛清被东厂番子一路拖进了幽深的詔狱长廊。
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,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只见大理寺少卿郑笔畅正与东厂提督曹至淳在廊下说话。
“郑兄!郑兄救我。“
閆矛清突然挣扎著大喊道。
“您帮小弟给誉王带个话,让他搭救小弟出去啊!“
郑笔畅闻声转头,待看清是閆矛清后,脸色骤然一变。
接著他迅速別过脸去,装作没听见。
一旁的曹至淳笑问道:“郑大人,这位是您朋友?“
“不熟啊!“
郑笔畅一脸真挚地摇头,眼神清澈得像个孩子。
“这人怕是认错人了。“
曹至淳闻言会意一笑,躬身道:“咱家送大人出去。“
“有劳曹公公了。“郑笔畅拱手还礼,步履从容地跟著曹至淳往外走。
经过閆矛清身边时,他目不斜视,仿佛对方只是个不相干的囚犯。
出了詔狱大门,郑笔畅才长舒一口气。
他回头望了望阴森的詔狱大门,想起閆矛清那副狼狈相,不由得暗自庆幸。
幸亏自己机灵,没跟这蠢货扯上关係。
人家都说大智若愚,这閆矛清倒好,整个一大愚弱智。
活该有此一劫!
“呃!!!”
閆矛清双目圆睁,难以置信的盯著郑笔畅的背影
曾经与他称兄道弟的郑笔畅此时竟装作素不相识的模样。
閆矛清张了张嘴,却不知该说什么。
直到他被粗暴地拖拽到刑架面前,铁链缠上手腕时,他才猛然惊醒。
“你们要干什么?”
閆矛清拼命挣扎,色厉內荏的叫囂道。
“我可是誉王殿下的人,你们知道得罪誉王的下场吗?”
他咽了口唾沫,强自镇定地继续喊道:“我在朝中的人脉岂是你们能想像的,刑部齐敏大人是我至交,吏部何敬中大人与我称兄道弟。”
“若是让他们知道你们敢对我用私刑…”
话音未落,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。
只见曹至淳负手踱入刑房,慢条斯理的开口道:“閆大人好大的威风啊!”
“曹公公,我人脉广,我认识…”
閆矛清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曹至淳直接打断。
“別张口人脉闭口人脉的,人脉再牛,跟你有什么关係啊!”
曹至淳笑著拿起一把带倒刺的长鞭,走到閆矛清面前。
“哟,忘了跟您说了。”
“我他娘的跟皇上还一单位呢,有他妈什么用啊!”
“哪位娘娘也没瞧上我啊!”
“是吧!”
閆矛清闻言,瞳孔猛的一颤,整个人呆若木鸡。
他万万没想到,自己搬出誉王、刑部、吏部这么多大人物的名號,曹至淳竟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
半点情面都不留。
下一秒,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。
曹至淳冷笑一声,懒得再与他废话,直接挥起长鞭。
啪!
带著倒刺的鞭子破空抽下,狠狠落在閆矛清身上。
皮开肉绽的声音伴隨著他悽厉的惨叫在刑房里迴荡。
“啊啊啊!!!”
“说不说?”
“说不说?”
“说不说?”
…
曹至淳每问一句,鞭子就跟著抽一下,根本不给閆矛清喘息的机会。
“啊!啊!你倒是问啊!”
閆矛清疼得浑身抽搐,终於崩溃地嘶吼出声。
“我没问吗?”
曹至淳疑惑地看了看手中的鞭子,隨即又是一鞭子狠狠抽下。
啪!
閆矛清疼得惨叫连连,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“我还没问,就想打你,说明你是真欠打。”
曹至淳慢悠悠地说道。
紧接著,转头对旁边的狱卒吩咐道:“来,轮流打,打满半个时辰。”
“不要,我什么都说。”
“我有罪!我认罪!求求你们別打了!”
剎那间,閆矛清便彻底崩溃,哭喊著求饶,声音里满是绝望和恐惧。
曹至淳这才问道:“东西呢?”
“什么?”
“看来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吶,我问你金子呢?”
反正閆矛清已经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,不如废物利用,先拿来顶一次锅。
可怜閆矛清还不知道自己被卖了。
听说是誉王特地嘱咐的,还以为能够同时攀上了誉王、齐敏和何敬中三个大人物。
京兆尹府才將何文新移送到刑部,他便屁顛屁顛的替其偽造证据。
说来也是巧。
閆矛清前脚才把何文新用罐子砸死邱泽的命案,硬生生改成了“邱泽酒后失足,不慎撞上罐子自尽“。
正得意自己的杰作,幻想著巴结上誉王从此一步登天。
后脚东厂的番子就闯进来了。
閆矛清抬头只见一队东厂番子鱼贯而入,为首的档头手持铁链,冷笑连连。
“閆矛清,涉嫌庆国公一案查抄时贪墨,抓起来。“
档头一声令下,几个番子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。
“誒!你们干什么。“
閆矛清被按在地上,还在拼命挣扎。
“凭什么抓我,我没有贪墨,我没有贪墨啊!“
档头冷笑一声,一脚踩在他背上。
“有没有贪墨,可不是你说了算的,带走!“
“等等!“
閆矛清突然扯著嗓子嚎叫。
“我上头有人,我上头有人!“
这话一出,只见那群东厂番子突然“噌噌噌“全部拔刀。
一个个跟猴子似的躥上了屋顶。
轰隆!
年久失修的屋顶哪经得起这番折腾。
整个房顶轰然塌陷,瓦片木樑劈头盖脸砸下来。
把閆矛清砸得头破血流。
“你个表…“
档头从废墟里爬出来,拍著身上的灰,气冲冲走到閆矛清面前。
“上头哪有人?”
“敢骗东厂,等死吧你!”
说著抬手就是两个响亮的大耳刮子,打得閆矛清眼冒金星。
“带走!“
他大手一挥,几个灰头土脸的番子从废墟里钻出来。
拖著彻底懵逼的閆矛清就往外走。
齐敏此刻正猫著腰躲在值房中,一只眼睛紧贴著窗缝看著外面。
看著閆矛清像条死狗似的被东厂拖走,他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上翘,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。
心里美得跟吃了蜜蜂屎似的。
这下子,何文新那小子也按誉王的意思放了。
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沾过案子,誉王和何敬之还得呈他的情。
最后,他还成功的让閆矛清那个蠢货把黑锅背得严严实实。
就算將来有人要翻旧帐,那也只能查到死人头上。
他可不认为,閆矛清进了詔狱,还能有机会活著走出来。
“我可真是个小天才。”
他舒舒服服的躺在太师椅上,美滋滋地唱起小曲来。
閆矛清被东厂番子一路拖进了幽深的詔狱长廊。
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,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只见大理寺少卿郑笔畅正与东厂提督曹至淳在廊下说话。
“郑兄!郑兄救我。“
閆矛清突然挣扎著大喊道。
“您帮小弟给誉王带个话,让他搭救小弟出去啊!“
郑笔畅闻声转头,待看清是閆矛清后,脸色骤然一变。
接著他迅速別过脸去,装作没听见。
一旁的曹至淳笑问道:“郑大人,这位是您朋友?“
“不熟啊!“
郑笔畅一脸真挚地摇头,眼神清澈得像个孩子。
“这人怕是认错人了。“
曹至淳闻言会意一笑,躬身道:“咱家送大人出去。“
“有劳曹公公了。“郑笔畅拱手还礼,步履从容地跟著曹至淳往外走。
经过閆矛清身边时,他目不斜视,仿佛对方只是个不相干的囚犯。
出了詔狱大门,郑笔畅才长舒一口气。
他回头望了望阴森的詔狱大门,想起閆矛清那副狼狈相,不由得暗自庆幸。
幸亏自己机灵,没跟这蠢货扯上关係。
人家都说大智若愚,这閆矛清倒好,整个一大愚弱智。
活该有此一劫!
“呃!!!”
閆矛清双目圆睁,难以置信的盯著郑笔畅的背影
曾经与他称兄道弟的郑笔畅此时竟装作素不相识的模样。
閆矛清张了张嘴,却不知该说什么。
直到他被粗暴地拖拽到刑架面前,铁链缠上手腕时,他才猛然惊醒。
“你们要干什么?”
閆矛清拼命挣扎,色厉內荏的叫囂道。
“我可是誉王殿下的人,你们知道得罪誉王的下场吗?”
他咽了口唾沫,强自镇定地继续喊道:“我在朝中的人脉岂是你们能想像的,刑部齐敏大人是我至交,吏部何敬中大人与我称兄道弟。”
“若是让他们知道你们敢对我用私刑…”
话音未落,沉重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。
只见曹至淳负手踱入刑房,慢条斯理的开口道:“閆大人好大的威风啊!”
“曹公公,我人脉广,我认识…”
閆矛清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曹至淳直接打断。
“別张口人脉闭口人脉的,人脉再牛,跟你有什么关係啊!”
曹至淳笑著拿起一把带倒刺的长鞭,走到閆矛清面前。
“哟,忘了跟您说了。”
“我他娘的跟皇上还一单位呢,有他妈什么用啊!”
“哪位娘娘也没瞧上我啊!”
“是吧!”
閆矛清闻言,瞳孔猛的一颤,整个人呆若木鸡。
他万万没想到,自己搬出誉王、刑部、吏部这么多大人物的名號,曹至淳竟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
半点情面都不留。
下一秒,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。
曹至淳冷笑一声,懒得再与他废话,直接挥起长鞭。
啪!
带著倒刺的鞭子破空抽下,狠狠落在閆矛清身上。
皮开肉绽的声音伴隨著他悽厉的惨叫在刑房里迴荡。
“啊啊啊!!!”
“说不说?”
“说不说?”
“说不说?”
…
曹至淳每问一句,鞭子就跟著抽一下,根本不给閆矛清喘息的机会。
“啊!啊!你倒是问啊!”
閆矛清疼得浑身抽搐,终於崩溃地嘶吼出声。
“我没问吗?”
曹至淳疑惑地看了看手中的鞭子,隨即又是一鞭子狠狠抽下。
啪!
閆矛清疼得惨叫连连,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“我还没问,就想打你,说明你是真欠打。”
曹至淳慢悠悠地说道。
紧接著,转头对旁边的狱卒吩咐道:“来,轮流打,打满半个时辰。”
“不要,我什么都说。”
“我有罪!我认罪!求求你们別打了!”
剎那间,閆矛清便彻底崩溃,哭喊著求饶,声音里满是绝望和恐惧。
曹至淳这才问道:“东西呢?”
“什么?”
“看来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吶,我问你金子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