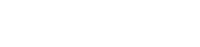待严东楼將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,朱厚聪才恍然大悟。
五年前,南楚皇后薨逝时,曾发生过一桩惊天秘闻。
当时太子宇文权不知为何,被皇帝刻意阻拦在宫外,不得见生母最后一面。
情急之下,太子竟与表弟兴安伯顾惜朝合谋,假传边关紧急军情,骗开了宫门。
此举虽成全了太子的孝心,却也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。
本该在五年前举行的冠礼,也因此被整整推迟了五年。
直到前几日,在吏部尚书卢世煜率领百官跪諫之下,南楚皇帝这才同意为太子行冠礼。
说好听一点是跪諫,其实就是逼宫。
皇帝宇文鉴连下三道口諭,命这些大臣速速退下。
可这些人却置若罔闻,一个个跪在殿外纹丝不动。
换做朱厚聪,早就开门放曹至淳了。
棍棒底下出孝子。
臣子不听话,就得用大棒招呼。
可南楚的皇帝终究没有这个魄力。
不过,紧接著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。
当太子宇文权的身影出现在殿外时,方才这些连圣旨都不听的官员。
被太子一说,就乖乖的退下了。
这般鲜明的对比,也难怪宇文鉴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忌惮至此。
这般功高震主,哪个帝王能安然处之?
而齐王那边也是奇葩,为了继续阻挠这场迟来的冠礼,竟与深宫中一个经常通姦的小宫女暗中勾结。
精心炮製了一份假文书,来控诉太子五年之前那桩不忠不孝的事情。
打算在冠礼现场当眾掷出,好让太子与皇帝顏面扫地。
可惜太子棋高一著,將那名宫女策反,反將一军,差点把齐王送进了宗人府。
今天在朝堂之上,严东楼见太子受挫,竟然一度以为优势在我。
急功近利,当庭进言请求废储。
朱厚聪听罢,不禁哑然失笑。
这般鲁莽行径,倒真是像极了小阁老的作风。
听完整个来龙去脉,朱厚聪只觉得槽点无数,雷得人外焦里嫩的。
最雷人的一点,就是南楚老皇帝对齐王宇文棠的偏宠。
皇子和宫女通姦…
这三个词分开他都认识,可他们是怎么组合成一句话的。
要知道,宫中宫女名义上可都是皇帝的女人。
皇子染指宫女,简直就是在给皇帝戴绿帽子。
放在哪个朝代不是大逆不道?
偏偏这位老皇帝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朱厚聪越想越觉得荒谬。
这要换作大梁,轻则圈禁,重则废为庶人。
可这位老皇帝倒好,非但不严惩,反倒还像个没事人一样。
而他对太子宇文权却又是另外一副面孔。
不过是为了见母后最后一面假传军情骗开宫门,就被圈禁五年。
两相对比之下,这偏心的程度简直令人髮指。
也难怪齐王敢如此肆无忌惮。
朱厚聪眼中闪过一抹讥讽之色。
有这么一个毫无原则的护短父皇撑腰,换谁不得飘上天?
不过,对於朱厚聪来说,南楚皇室越乱,对他越有利。
父子离心,兄弟鬩墙,不就是天赐的良机。
他暗自盘算著,回想起前世那部剧中太子被逼到绝路的整个过程。
只要继续暗中推波助澜,復刻出剧中整死太子的过程。
不就能够让这对相爱相杀的父子必兵戎相见嘛!
到那时,他只需带著宇文喧挥师南下擒龙,诛灭宇文一族,不就可以坐收渔利了。
於是朱厚聪操控著青龙说道:“严大人,废立储君非同儿戏。”
“要想撼动太子之位,必先剪除其羽翼,断其爪牙,方能成事。”
严东楼闻言浑身一震,当即离席而起,深深一揖到地。
声音里带著几分急切。
“青龙先生乃当世奇才,还请不吝赐教,东楼愿闻其详。“
朱厚聪控制著青龙虚扶一把,胸有成竹的说道:“严大人不必多礼。”
“某与大人初见时便说过,要送齐王殿下一顶'白'帽子,此时自当竭尽全力。“
严东楼显然领会了朱厚聪话中深意。
“白“者,“皇“字去“王“也。
“眼下,便有一个难得一遇的良机。“
“先生请讲!“
“听闻此次春闈,武德侯之子,兴安伯顾惜朝也要下场应试?“
“不错,那顾惜朝虽出身將门,却有意考取功名,此次春闈確实报了名。“
青龙微微頷首,嘴角勾起一抹老谋深算的笑容。
“若是我们提前將考题泄露给他,会如何?“
严东楼闻言瞳孔一震。
“先生是说,借顾惜朝扳倒武德侯顾思凌?“
“非也非也。“
青龙轻摇手指。
“顾思凌手握二十万雄师镇守北疆长州,就算是为了边关安稳,陛下也绝不会动他的儿子顾惜朝一根汗毛。“
“那先生的意思是…“
“春闈主考官一向由吏部尚书卢世煜担任,我们只需將考题偷出,再栽赃给顾惜朝。”
“就能牵扯到太子身上,毕竟顾惜朝是太子的表弟。”
“而一旦牵扯到太子,卢世煜身为太子的老师,又是主考官,如何脱得了干係。”
此话一出,严东楼顿时眼前一亮,但隨即又面露难色。
“可考题存放之处,必然只有卢世煜一人知晓,我们如何偷得呢?“
“严大人这是当局者迷啊!“
青龙轻笑一声,替他分析道。
“三年一度的春闈,此次又是功勋子弟云集。”
“陛下怎会放心让卢世煜这位太子党第人一人主理?“
“太子的势力,已经让陛下寢食难安了。”
“若这一科进士尽成卢世煜门生,也就是太子的门生,那陛下可就连觉都睡不好了。“
“所以…“
青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盏,轻啜一口清茶。
“只需让齐王向陛下提议,此次春闈由严大人您共同主理,不就有机可乘了?“
“妙,妙啊!“
朱厚聪的计谋说完,严东楼当即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,先生稍作歇息,本官这就去安排!“
说罢,便急匆匆地往外走。
待严东楼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迴廊尽头,西苑精舍內的朱厚聪这才缓缓睁开双眼。
嘴角勾起一抹微笑。
这位严大人,嘴上说著感恩戴德,心里却还在防著他。
相当於变相软禁青龙在府中。
不过倒也无妨,自己只要帮他们彻底扳倒卢世煜这个太子党的中流砥柱。
齐王与严东楼自然会將他奉为上宾。
大梁这边借梅长苏之手整倒吏部尚书何敬中。
南楚那边则亲自设局,整倒南楚的吏部尚书卢世煜。
在这春闈来临之际,两个国家竟同时上演了一齣好戏。
五年前,南楚皇后薨逝时,曾发生过一桩惊天秘闻。
当时太子宇文权不知为何,被皇帝刻意阻拦在宫外,不得见生母最后一面。
情急之下,太子竟与表弟兴安伯顾惜朝合谋,假传边关紧急军情,骗开了宫门。
此举虽成全了太子的孝心,却也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。
本该在五年前举行的冠礼,也因此被整整推迟了五年。
直到前几日,在吏部尚书卢世煜率领百官跪諫之下,南楚皇帝这才同意为太子行冠礼。
说好听一点是跪諫,其实就是逼宫。
皇帝宇文鉴连下三道口諭,命这些大臣速速退下。
可这些人却置若罔闻,一个个跪在殿外纹丝不动。
换做朱厚聪,早就开门放曹至淳了。
棍棒底下出孝子。
臣子不听话,就得用大棒招呼。
可南楚的皇帝终究没有这个魄力。
不过,紧接著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。
当太子宇文权的身影出现在殿外时,方才这些连圣旨都不听的官员。
被太子一说,就乖乖的退下了。
这般鲜明的对比,也难怪宇文鉴会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忌惮至此。
这般功高震主,哪个帝王能安然处之?
而齐王那边也是奇葩,为了继续阻挠这场迟来的冠礼,竟与深宫中一个经常通姦的小宫女暗中勾结。
精心炮製了一份假文书,来控诉太子五年之前那桩不忠不孝的事情。
打算在冠礼现场当眾掷出,好让太子与皇帝顏面扫地。
可惜太子棋高一著,將那名宫女策反,反將一军,差点把齐王送进了宗人府。
今天在朝堂之上,严东楼见太子受挫,竟然一度以为优势在我。
急功近利,当庭进言请求废储。
朱厚聪听罢,不禁哑然失笑。
这般鲁莽行径,倒真是像极了小阁老的作风。
听完整个来龙去脉,朱厚聪只觉得槽点无数,雷得人外焦里嫩的。
最雷人的一点,就是南楚老皇帝对齐王宇文棠的偏宠。
皇子和宫女通姦…
这三个词分开他都认识,可他们是怎么组合成一句话的。
要知道,宫中宫女名义上可都是皇帝的女人。
皇子染指宫女,简直就是在给皇帝戴绿帽子。
放在哪个朝代不是大逆不道?
偏偏这位老皇帝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朱厚聪越想越觉得荒谬。
这要换作大梁,轻则圈禁,重则废为庶人。
可这位老皇帝倒好,非但不严惩,反倒还像个没事人一样。
而他对太子宇文权却又是另外一副面孔。
不过是为了见母后最后一面假传军情骗开宫门,就被圈禁五年。
两相对比之下,这偏心的程度简直令人髮指。
也难怪齐王敢如此肆无忌惮。
朱厚聪眼中闪过一抹讥讽之色。
有这么一个毫无原则的护短父皇撑腰,换谁不得飘上天?
不过,对於朱厚聪来说,南楚皇室越乱,对他越有利。
父子离心,兄弟鬩墙,不就是天赐的良机。
他暗自盘算著,回想起前世那部剧中太子被逼到绝路的整个过程。
只要继续暗中推波助澜,復刻出剧中整死太子的过程。
不就能够让这对相爱相杀的父子必兵戎相见嘛!
到那时,他只需带著宇文喧挥师南下擒龙,诛灭宇文一族,不就可以坐收渔利了。
於是朱厚聪操控著青龙说道:“严大人,废立储君非同儿戏。”
“要想撼动太子之位,必先剪除其羽翼,断其爪牙,方能成事。”
严东楼闻言浑身一震,当即离席而起,深深一揖到地。
声音里带著几分急切。
“青龙先生乃当世奇才,还请不吝赐教,东楼愿闻其详。“
朱厚聪控制著青龙虚扶一把,胸有成竹的说道:“严大人不必多礼。”
“某与大人初见时便说过,要送齐王殿下一顶'白'帽子,此时自当竭尽全力。“
严东楼显然领会了朱厚聪话中深意。
“白“者,“皇“字去“王“也。
“眼下,便有一个难得一遇的良机。“
“先生请讲!“
“听闻此次春闈,武德侯之子,兴安伯顾惜朝也要下场应试?“
“不错,那顾惜朝虽出身將门,却有意考取功名,此次春闈確实报了名。“
青龙微微頷首,嘴角勾起一抹老谋深算的笑容。
“若是我们提前將考题泄露给他,会如何?“
严东楼闻言瞳孔一震。
“先生是说,借顾惜朝扳倒武德侯顾思凌?“
“非也非也。“
青龙轻摇手指。
“顾思凌手握二十万雄师镇守北疆长州,就算是为了边关安稳,陛下也绝不会动他的儿子顾惜朝一根汗毛。“
“那先生的意思是…“
“春闈主考官一向由吏部尚书卢世煜担任,我们只需將考题偷出,再栽赃给顾惜朝。”
“就能牵扯到太子身上,毕竟顾惜朝是太子的表弟。”
“而一旦牵扯到太子,卢世煜身为太子的老师,又是主考官,如何脱得了干係。”
此话一出,严东楼顿时眼前一亮,但隨即又面露难色。
“可考题存放之处,必然只有卢世煜一人知晓,我们如何偷得呢?“
“严大人这是当局者迷啊!“
青龙轻笑一声,替他分析道。
“三年一度的春闈,此次又是功勋子弟云集。”
“陛下怎会放心让卢世煜这位太子党第人一人主理?“
“太子的势力,已经让陛下寢食难安了。”
“若这一科进士尽成卢世煜门生,也就是太子的门生,那陛下可就连觉都睡不好了。“
“所以…“
青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盏,轻啜一口清茶。
“只需让齐王向陛下提议,此次春闈由严大人您共同主理,不就有机可乘了?“
“妙,妙啊!“
朱厚聪的计谋说完,严东楼当即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,先生稍作歇息,本官这就去安排!“
说罢,便急匆匆地往外走。
待严东楼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迴廊尽头,西苑精舍內的朱厚聪这才缓缓睁开双眼。
嘴角勾起一抹微笑。
这位严大人,嘴上说著感恩戴德,心里却还在防著他。
相当於变相软禁青龙在府中。
不过倒也无妨,自己只要帮他们彻底扳倒卢世煜这个太子党的中流砥柱。
齐王与严东楼自然会將他奉为上宾。
大梁这边借梅长苏之手整倒吏部尚书何敬中。
南楚那边则亲自设局,整倒南楚的吏部尚书卢世煜。
在这春闈来临之际,两个国家竟同时上演了一齣好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