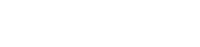天还没亮透,紫宸殿里已经黑压压跪了一地。
这哪是早朝,这分明是弔丧。
空气里那股子龙涎香,被昨日那个烧焦的信使留下的血腥和焦臭味冲得七零八落。
闻著就让人犯噁心。
昨日还人五人六、指点江山的平南侯田左牧,此刻像条被打断了脊樑的死狗。
直挺挺地跪在大殿正中央。
他头上的紫金冠早就没了,髮髻散乱,一身名贵的锦绣朝服蹭满了灰尘和口水。
“田左牧!你这国贼!!”
一名断了条胳膊、脸上还缠著带血麻布的京营武將,挣扎著从队列里衝出来。
一口浓痰不偏不倚地啐在田左牧的脸上。
“老子的三万兄弟!三万个活生生的人!就因为你那狗屁的『养寇自重』,全他妈葬身在北境那鬼地方。
你拿什么赔?你拿你全家老小的命来赔都不够!!”
武將吼得声嘶力竭,眼珠子红得快要冒血。
田左牧浑身一颤,黏糊糊的痰顺著他煞白的脸流下来。
他却连擦都不敢擦,只是一个劲儿地把脑门往冰冷坚硬的金砖地上磕。
“砰!砰!砰!”
“臣有罪……臣罪该万死……求陛下开恩……”
他现在脑子里啥都没有,就记得那个叫陈远的男人,还有那从天而降烧光一切的妖火。
他百口莫辩,除了磕头,屁都放不出一个。
龙椅上,新帝柴启的脸色比田左牧还白,嘴唇哆嗦著。
一夜之间,仿佛老了十岁。
“报仇!陛下!必须报仇!”
那断臂武將跪在地上,对著龙椅嘶吼。
“倾全国之兵!跟那陈远决一死战!不把他剁成肉酱,我大夏军魂何在?!”
“没错!决一死战!”
殿阶下,一群武將跟著红了眼,嚷嚷著要拼命。
“放屁!”
鬚髮皆白的老太傅王朗拄著拐杖,颤巍巍地走出来。
拐杖狠狠一顿地,发出沉闷的响声,竟压下了满殿的叫囂。
他老眼里含著泪,嗓子哑得像拉破风箱:“拿什么战?拿你们的嘴去战吗?!”
他环视一圈,一字一顿,每个字都像一块冰砸在眾人心上。
“户部帐上,还剩不足二十万两现银!连京城所有卫戍部队三个月的餉银都发不出来!”
“刘成带走的那三万京营,几乎掏空了我们京畿所有的精锐和粮草!”
“现在再打?北边的戎狄蛮子怕不是要笑得从床上滚下来。等著咱们跟陈远拼个两败俱伤,他们好直接挥师南下,到这临安城里来喝酒吃肉!”
“江山……危在旦夕啊!陛下!”
老太傅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老泪纵横。
“江山危在旦夕”这六个字,像六把尖刀。
狠狠扎进了柴启的心窝子。
报仇?他现在哪还敢想报仇!
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
那个能召唤妖火的魔鬼,会不会下一刻就兵临城下,把他从这张龙椅上揪下来,也扔进火里烧成焦炭?
他怕了,怕得要死。
“和……和谈!”柴启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,声音尖利得变了调,“立刻跟陈远和谈!他要什么,就给他什么!稳住他!必须稳住他!”
话音一落,刚刚还喊打喊杀的武將们瞬间哑了火。
而那些文臣,则像是闻到腥味的苍蝇,立刻活跃起来。
“陛下圣明!臣以为,当立刻下旨,赏金十万两,绸缎千匹!”
“不够!那陈远胃口极大,十万两怕是打发不了叫花子!臣以为,当割让鹤陟县以北三州之地,以示诚意!”
“放屁!土地乃国之根本,岂可轻与?依臣看,不如加封他为『北境王』,许他世袭罔替!”
大殿之上,瞬间变成了一个屈辱的拍卖场。
这群刚才还噤若寒蝉的大臣,此刻爭先恐后地叫卖著大夏的尊严和財富,仿佛谁卖得最狠,谁就最忠心。
就在这时。
一个角落里的小官灵机一动,突然高声道:“陛下!臣记起来了!那逆……那陈將军身边,似乎一直跟著四皇女殿下!”
轰!
这话点醒了混沌的柴启。
对啊!柴沅!
那个他最瞧不起,早就当成弃子扔到北境的妹妹!
“快说!你的主意!”柴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死死盯著那个小官。
那小官被皇帝的眼神看得一哆嗦,连忙跪下道:“陛下可下旨,正式册封陈远为『护国駙马』!再追封四皇女为长公主!
如此一来,他陈远便是我皇室之人,从法理上,他就是我大夏的臣子!
再反,就是乱臣贼子,天下共击之!”
好主意!
柴启的眼睛瞬间亮了!
这简直是神来之笔!用一个名分,就把那头恶狼套上了项圈!
“好!好!”
柴启龙顏大悦,一巴掌拍在龙椅扶手上,“不仅如此!传朕旨意,再从宗室和朝中勛贵里,挑选十二名年纪最轻、容貌最美的绝色女子,一併打包,作为贺礼送去齐州!”
“朕要让他知道,什么叫皇恩浩荡!”
赏赐和名分都定下了,最关键的问题来了。
谁去?
柴启的目光扫过全场,声音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:“哪位爱卿,愿为朕分忧,走这一趟?”
大殿之內,瞬间鸦雀无声。
刚才还爭先恐后出谋划策的大臣们,此刻一个个低著头。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襠里,生怕被皇帝看到。
开什么玩笑?
上一任钦差刘成,带著三万大军都化成了灰。
现在自己一个人去?那不是去传旨,那是去投胎!
看著满朝的软骨头,柴启的脸一阵青一阵白,心头的怒火和恐惧交织。
他的目光缓缓移动,最终像鹰隼一样。
死死锁在了大殿角落里,一个正拼命缩入柱子影子的人身上。
內廷卫指挥使——李德福。
“李伴伴。”
柴启声音不高,可听在李德福耳朵里,跟催命符似的。
“你……你与那陈远,有过一面之缘,熟悉情况。就由你,代朕,再去一趟吧。”
李德福瞬间嚇得浑身冰凉。
他想起在齐州的遭遇。姓王的老管家抱著他的腿哭嚎,张姜將军当面要三成金库,吕方明连见都懒得见他……
最后,是陈远那张带著戏謔微笑的脸。
那不是人,那是一群魔鬼!
“噗通!”
李德福双腿一软,瘫倒在地,一股骚臭的液体,瞬间浸湿了他名贵的官袍。
他,当场嚇尿了。
“不……奴婢不去……陛下饶命啊!”
李德福连滚带爬扑到龙椅前。
涕泗横流,半点钦差威仪都不剩。
“那齐州就是个龙潭虎穴!
陈远麾下那帮人,个个都是不讲道理的虎狼!
奴婢再去,就是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啊!
求陛下换个人去吧!求您了!”
看著脚下这个哭得像个三岁孩子的废物,柴启的脸,彻底冷了下来。
他需要一个替罪羊,更需要一个能把这份屈辱的圣旨,这个烫手的山芋,送出去的人。
李德福,就是最好的人选。
他缓缓走下龙椅,亲自將瘫软如泥的李德福扶了起来,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最亲密的爱人。
他凑到李德福的耳边,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,阴冷地,一字一顿地说道:
“你此去,若能安抚住他,让他俯首称臣。”
“回来,你便是司礼监掌印大太监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里的温度降到了冰点。
“若安抚不住……”
“朕的京城,也不需要一个连差事都办不好的……废物。”
李德福的哭声,戛然而止。
他僵硬地抬起头,看著皇帝那双不带丝毫感情的眼睛,脸上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。
去是死。
不去,也是死。
甚至,会死得更惨。
这哪是早朝,这分明是弔丧。
空气里那股子龙涎香,被昨日那个烧焦的信使留下的血腥和焦臭味冲得七零八落。
闻著就让人犯噁心。
昨日还人五人六、指点江山的平南侯田左牧,此刻像条被打断了脊樑的死狗。
直挺挺地跪在大殿正中央。
他头上的紫金冠早就没了,髮髻散乱,一身名贵的锦绣朝服蹭满了灰尘和口水。
“田左牧!你这国贼!!”
一名断了条胳膊、脸上还缠著带血麻布的京营武將,挣扎著从队列里衝出来。
一口浓痰不偏不倚地啐在田左牧的脸上。
“老子的三万兄弟!三万个活生生的人!就因为你那狗屁的『养寇自重』,全他妈葬身在北境那鬼地方。
你拿什么赔?你拿你全家老小的命来赔都不够!!”
武將吼得声嘶力竭,眼珠子红得快要冒血。
田左牧浑身一颤,黏糊糊的痰顺著他煞白的脸流下来。
他却连擦都不敢擦,只是一个劲儿地把脑门往冰冷坚硬的金砖地上磕。
“砰!砰!砰!”
“臣有罪……臣罪该万死……求陛下开恩……”
他现在脑子里啥都没有,就记得那个叫陈远的男人,还有那从天而降烧光一切的妖火。
他百口莫辩,除了磕头,屁都放不出一个。
龙椅上,新帝柴启的脸色比田左牧还白,嘴唇哆嗦著。
一夜之间,仿佛老了十岁。
“报仇!陛下!必须报仇!”
那断臂武將跪在地上,对著龙椅嘶吼。
“倾全国之兵!跟那陈远决一死战!不把他剁成肉酱,我大夏军魂何在?!”
“没错!决一死战!”
殿阶下,一群武將跟著红了眼,嚷嚷著要拼命。
“放屁!”
鬚髮皆白的老太傅王朗拄著拐杖,颤巍巍地走出来。
拐杖狠狠一顿地,发出沉闷的响声,竟压下了满殿的叫囂。
他老眼里含著泪,嗓子哑得像拉破风箱:“拿什么战?拿你们的嘴去战吗?!”
他环视一圈,一字一顿,每个字都像一块冰砸在眾人心上。
“户部帐上,还剩不足二十万两现银!连京城所有卫戍部队三个月的餉银都发不出来!”
“刘成带走的那三万京营,几乎掏空了我们京畿所有的精锐和粮草!”
“现在再打?北边的戎狄蛮子怕不是要笑得从床上滚下来。等著咱们跟陈远拼个两败俱伤,他们好直接挥师南下,到这临安城里来喝酒吃肉!”
“江山……危在旦夕啊!陛下!”
老太傅“噗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老泪纵横。
“江山危在旦夕”这六个字,像六把尖刀。
狠狠扎进了柴启的心窝子。
报仇?他现在哪还敢想报仇!
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。
那个能召唤妖火的魔鬼,会不会下一刻就兵临城下,把他从这张龙椅上揪下来,也扔进火里烧成焦炭?
他怕了,怕得要死。
“和……和谈!”柴启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,声音尖利得变了调,“立刻跟陈远和谈!他要什么,就给他什么!稳住他!必须稳住他!”
话音一落,刚刚还喊打喊杀的武將们瞬间哑了火。
而那些文臣,则像是闻到腥味的苍蝇,立刻活跃起来。
“陛下圣明!臣以为,当立刻下旨,赏金十万两,绸缎千匹!”
“不够!那陈远胃口极大,十万两怕是打发不了叫花子!臣以为,当割让鹤陟县以北三州之地,以示诚意!”
“放屁!土地乃国之根本,岂可轻与?依臣看,不如加封他为『北境王』,许他世袭罔替!”
大殿之上,瞬间变成了一个屈辱的拍卖场。
这群刚才还噤若寒蝉的大臣,此刻爭先恐后地叫卖著大夏的尊严和財富,仿佛谁卖得最狠,谁就最忠心。
就在这时。
一个角落里的小官灵机一动,突然高声道:“陛下!臣记起来了!那逆……那陈將军身边,似乎一直跟著四皇女殿下!”
轰!
这话点醒了混沌的柴启。
对啊!柴沅!
那个他最瞧不起,早就当成弃子扔到北境的妹妹!
“快说!你的主意!”柴启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死死盯著那个小官。
那小官被皇帝的眼神看得一哆嗦,连忙跪下道:“陛下可下旨,正式册封陈远为『护国駙马』!再追封四皇女为长公主!
如此一来,他陈远便是我皇室之人,从法理上,他就是我大夏的臣子!
再反,就是乱臣贼子,天下共击之!”
好主意!
柴启的眼睛瞬间亮了!
这简直是神来之笔!用一个名分,就把那头恶狼套上了项圈!
“好!好!”
柴启龙顏大悦,一巴掌拍在龙椅扶手上,“不仅如此!传朕旨意,再从宗室和朝中勛贵里,挑选十二名年纪最轻、容貌最美的绝色女子,一併打包,作为贺礼送去齐州!”
“朕要让他知道,什么叫皇恩浩荡!”
赏赐和名分都定下了,最关键的问题来了。
谁去?
柴启的目光扫过全场,声音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:“哪位爱卿,愿为朕分忧,走这一趟?”
大殿之內,瞬间鸦雀无声。
刚才还爭先恐后出谋划策的大臣们,此刻一个个低著头。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襠里,生怕被皇帝看到。
开什么玩笑?
上一任钦差刘成,带著三万大军都化成了灰。
现在自己一个人去?那不是去传旨,那是去投胎!
看著满朝的软骨头,柴启的脸一阵青一阵白,心头的怒火和恐惧交织。
他的目光缓缓移动,最终像鹰隼一样。
死死锁在了大殿角落里,一个正拼命缩入柱子影子的人身上。
內廷卫指挥使——李德福。
“李伴伴。”
柴启声音不高,可听在李德福耳朵里,跟催命符似的。
“你……你与那陈远,有过一面之缘,熟悉情况。就由你,代朕,再去一趟吧。”
李德福瞬间嚇得浑身冰凉。
他想起在齐州的遭遇。姓王的老管家抱著他的腿哭嚎,张姜將军当面要三成金库,吕方明连见都懒得见他……
最后,是陈远那张带著戏謔微笑的脸。
那不是人,那是一群魔鬼!
“噗通!”
李德福双腿一软,瘫倒在地,一股骚臭的液体,瞬间浸湿了他名贵的官袍。
他,当场嚇尿了。
“不……奴婢不去……陛下饶命啊!”
李德福连滚带爬扑到龙椅前。
涕泗横流,半点钦差威仪都不剩。
“那齐州就是个龙潭虎穴!
陈远麾下那帮人,个个都是不讲道理的虎狼!
奴婢再去,就是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啊!
求陛下换个人去吧!求您了!”
看著脚下这个哭得像个三岁孩子的废物,柴启的脸,彻底冷了下来。
他需要一个替罪羊,更需要一个能把这份屈辱的圣旨,这个烫手的山芋,送出去的人。
李德福,就是最好的人选。
他缓缓走下龙椅,亲自將瘫软如泥的李德福扶了起来,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最亲密的爱人。
他凑到李德福的耳边,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,阴冷地,一字一顿地说道:
“你此去,若能安抚住他,让他俯首称臣。”
“回来,你便是司礼监掌印大太监。”
他顿了顿,语气里的温度降到了冰点。
“若安抚不住……”
“朕的京城,也不需要一个连差事都办不好的……废物。”
李德福的哭声,戛然而止。
他僵硬地抬起头,看著皇帝那双不带丝毫感情的眼睛,脸上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。
去是死。
不去,也是死。
甚至,会死得更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