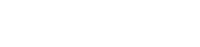次日,郡守府大堂。
李德福特意换上了一身代表著皇权威仪的蟒纹大红袍,兰花指捏著明黄色的圣旨。
半眯著的眼睛里,满是即將看好戏的阴毒与快意。
他要的就是这个场面!
当著齐州所有头面人物的面,让陈远跪下,让他低头,让他明白。
不管他在北境这片烂泥地里怎么折腾,在天子面前,他终究只是一条隨时能被捏死的狗!
香案摆开,薰香繚绕。
“宣——旨——!”
李德福扯著他那又尖又细的嗓子,故意拉长了音调,眼神冷得像刀,死死盯著堂下的陈远。
“齐州守將陈远,接旨!”
陈远一身戎装,闻言,毫不犹豫,撩起战袍下摆,单膝跪地。
他身后的张姜、冯四娘,乃至刚刚从白云山大胜归来、一身煞气的吕方明。
也都齐刷刷地单膝跪下。
动作规规矩矩,半点儿错都挑不出来。
可李德福的脸,一下子就沉了。
跪是跪了。
但不对劲!
陈远腰杆挺得笔直,微微抬著头,眼神平静得很。
哪有半分见圣旨该有的惶恐?分明是在审视!
他身后的那几员悍將,更是个个煞气內敛,眼神凶得很,跪在那儿不像接旨,倒像隨时要扑上来的老虎!
这哪里是跪迎,这分明是示威!
李德福心头火起,捏著圣旨的指节都泛白了,但他脸上依旧掛著假笑,开始念诵那篇写得冠冕堂皇却藏著算计的圣旨。
无非是先夸陈远“守土有功”,再赏了个不痛不痒的“破虏將军”虚衔。
最后话锋一转,就变成了敲打,要他“恪守臣节,戒骄戒躁,好生辅佐钦差,查验军务,以安圣心”。
“臣,陈远,谢陛下隆恩。”
陈远双手接过圣旨,语气平淡得跟说“今天天气挺好”似的,半点儿激动感激的样子都没有。
一拳,又打在了棉花上!
李德福一口老血堵在喉咙里,差点当场喷出来。
他强压下怒火,收起笑容,阴惻惻地开口:“陈將军,咱家奉陛下密令,需与將军麾下几位得力干將,单独敘敘。也好將他们的功绩,一併报与陛下知晓。”
分化瓦解的戏码,正式开锣!
“公公有请,末將岂敢不从。”陈远仿佛没听出弦外之音,一口应下。
……
半个时辰后,李德福下榻的別院。
张姜大马金刀地坐在李德福对面,对那套名贵的紫砂茶具看都懒得看一眼。
他自顾自地抓起盘子里最贵的几样宫廷点心,像是饿了三天一样,风捲残云般塞进嘴里。
吧唧吧唧……
清脆的咀嚼声,在安静的雅间里,显得格外刺耳。
李德福眼角狂抽,脸上那张皮笑肉不笑的面具都快掛不住了。
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武將!
终於,张姜吃完了最后一块桂花糕,抹了抹嘴,抬起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,直勾勾地看著李德福。
“说吧。”
“什么?”李德福一愣。
“公公想让我背刺將军,打算开什么价?”
张姜开门见山,语气像是在菜市场买白菜,“我先说好,没云州金库三成的好处,免谈。哦,对了,得是黄金,军票那玩意儿,我们自己印的,不稀罕。”
“噗——!”
李德福刚端起茶杯,一口热茶直接喷了出来,烫得他自己嗷嗷直叫。
他指著张姜,手指抖得跟筛糠似的,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这他娘的哪里是来密谈的,这分明是来打劫的!
张姜看著他那副德行,撇了撇嘴,站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渣。
“看来是谈不拢了。浪费时间。”
说完,她头也不回地走了,留下李德福一个人在风中凌乱,气得浑身发抖。
张姜这边刚走,一名小太监就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,哭丧著脸稟报。
“乾爹!那……那个破虏校尉吕方明,他……他拒不见您!”
“什么?!”
“他派亲卫回话,说……说將军令他操练兵马,军务在身,不敢与天使閒谈,怕误了军机!”
误了军机!
好一个误了军机!
这已经不是打脸了,这是指著鼻子骂他李德福一个太监,瞎掺和军国大事!
“反了!都反了!!”
李德福再也绷不住了,一把將桌上的名贵茶具全都扫落在地,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。
离间计,彻底破產!
“好!好一个陈远!你给咱家等著!”
李德福双眼血红,他知道,文的既然不行,那就只能来武的!
他猛地一拍桌子,对著门外尖叫道:“来人!传咱家將令!咱家要亲自巡查军备、清点粮册!咱家倒要看看,他陈远,拿什么来养这十万大军!”
这一次,陈远答应得比上次还痛快。
“公公一心为国,本將岂有不从之理?王朗!”
老管家王朗再次应声而出,脸上掛著忠厚老实的笑容:“將军,老奴在。”
“全力配合钦差大人!大人想看什么,就看什么!想查什么,就查什么!不得有误!”
“老奴……遵命!”
接下来的三天,成了李德福这辈子最大的噩梦。
王朗带著他去看帐本。
“哎呀!公公您瞧,这……这也不知哪来的耗子,把去年的帐本给啃了!罪过,罪过啊!”
王朗指著一堆碎纸屑,痛心疾首。
李德福去看粮仓。
“公公!真不巧!管仓库钥匙的那个兄弟,昨天喝多了,掉茅坑里了,钥匙……也跟著掉下去了!这会儿正叫人捞呢!”
王朗一脸的为难。
等好不容易找到备用钥匙,打开一座粮仓,里面空得能跑马。
“公公明鑑!这……这是咱们的疑兵之计!故意空出来的,就是为了迷惑戎狄探子!”
王朗说得头头是道,一脸“你真是个外行”的表情。
李德福被这老东西折腾得够呛,可人家理由编得圆,他连发火的由头都找不到!
而就在他被当猴耍得团团转的时候。
百里之外的鹤陟县,一线涧。
数千名振威营的士兵,和上万名自发前来的民夫,正热火朝天地吼著號子。
一车车由水泥被源源不断地浇筑进山体之中。
一座前所未见的雄关,在所有人的血汗浇灌下,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拔地而起!
第四天清晨。
李德福终於放弃了,他双眼布满血丝,整个人都瘦了一圈,失魂落魄地走在齐州城的街道上。
看著街道上车水马龙,百姓脸上洋溢著发自內心的笑容。
看著那些小贩和顾客,用军票交易时那份理所当然的信赖。
看著巡逻的士兵与百姓勾肩搭背,亲如一家……
一股寒意直窜头顶,凉透了骨头!
管理混乱?帐目不清?
放屁!
这分明是一种滴水不漏,配合默契到恐怖的阳谋!
他被耍了!从头到尾,他就像一个自作聪明的傻子,被陈远牵著鼻子,完美地避开了所有他想看到的东西!
“咕咚。”
李德福狠狠咽了口唾沫,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。
不能再待下去了!再待下去,自己这条命都得交代在这儿!
他当机立断,立刻返回郡守府,脸上立刻堆满了亲和的笑容,拉著陈远的手,亲热得像是见到了亲爹。
“陈將军!国之栋樑!国之栋樑啊!咱家这次回去,一定在陛下面前,为你好好请功!齐州军务安稳,百姓拥戴,咱家也该回京復命了!”
陈远看著他那拙劣的演技,同样笑得一脸真诚:“公公慢走,本將就不远送了。”
钦差仪仗,仓皇出城。
刚离开齐州地界,进入荒无人烟的山道。
李德福那张和善的脸,瞬间变得比恶鬼还要狰狞。
他猛地从袖中,掏出一只通体漆黑,眼神凶戾的信鸽。
飞快地在信管中塞入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。
扬手一挥,那只黑信鸽叫了一声,飞快地朝南边飞去!
李德福特意换上了一身代表著皇权威仪的蟒纹大红袍,兰花指捏著明黄色的圣旨。
半眯著的眼睛里,满是即將看好戏的阴毒与快意。
他要的就是这个场面!
当著齐州所有头面人物的面,让陈远跪下,让他低头,让他明白。
不管他在北境这片烂泥地里怎么折腾,在天子面前,他终究只是一条隨时能被捏死的狗!
香案摆开,薰香繚绕。
“宣——旨——!”
李德福扯著他那又尖又细的嗓子,故意拉长了音调,眼神冷得像刀,死死盯著堂下的陈远。
“齐州守將陈远,接旨!”
陈远一身戎装,闻言,毫不犹豫,撩起战袍下摆,单膝跪地。
他身后的张姜、冯四娘,乃至刚刚从白云山大胜归来、一身煞气的吕方明。
也都齐刷刷地单膝跪下。
动作规规矩矩,半点儿错都挑不出来。
可李德福的脸,一下子就沉了。
跪是跪了。
但不对劲!
陈远腰杆挺得笔直,微微抬著头,眼神平静得很。
哪有半分见圣旨该有的惶恐?分明是在审视!
他身后的那几员悍將,更是个个煞气內敛,眼神凶得很,跪在那儿不像接旨,倒像隨时要扑上来的老虎!
这哪里是跪迎,这分明是示威!
李德福心头火起,捏著圣旨的指节都泛白了,但他脸上依旧掛著假笑,开始念诵那篇写得冠冕堂皇却藏著算计的圣旨。
无非是先夸陈远“守土有功”,再赏了个不痛不痒的“破虏將军”虚衔。
最后话锋一转,就变成了敲打,要他“恪守臣节,戒骄戒躁,好生辅佐钦差,查验军务,以安圣心”。
“臣,陈远,谢陛下隆恩。”
陈远双手接过圣旨,语气平淡得跟说“今天天气挺好”似的,半点儿激动感激的样子都没有。
一拳,又打在了棉花上!
李德福一口老血堵在喉咙里,差点当场喷出来。
他强压下怒火,收起笑容,阴惻惻地开口:“陈將军,咱家奉陛下密令,需与將军麾下几位得力干將,单独敘敘。也好將他们的功绩,一併报与陛下知晓。”
分化瓦解的戏码,正式开锣!
“公公有请,末將岂敢不从。”陈远仿佛没听出弦外之音,一口应下。
……
半个时辰后,李德福下榻的別院。
张姜大马金刀地坐在李德福对面,对那套名贵的紫砂茶具看都懒得看一眼。
他自顾自地抓起盘子里最贵的几样宫廷点心,像是饿了三天一样,风捲残云般塞进嘴里。
吧唧吧唧……
清脆的咀嚼声,在安静的雅间里,显得格外刺耳。
李德福眼角狂抽,脸上那张皮笑肉不笑的面具都快掛不住了。
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不懂规矩的武將!
终於,张姜吃完了最后一块桂花糕,抹了抹嘴,抬起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,直勾勾地看著李德福。
“说吧。”
“什么?”李德福一愣。
“公公想让我背刺將军,打算开什么价?”
张姜开门见山,语气像是在菜市场买白菜,“我先说好,没云州金库三成的好处,免谈。哦,对了,得是黄金,军票那玩意儿,我们自己印的,不稀罕。”
“噗——!”
李德福刚端起茶杯,一口热茶直接喷了出来,烫得他自己嗷嗷直叫。
他指著张姜,手指抖得跟筛糠似的,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这他娘的哪里是来密谈的,这分明是来打劫的!
张姜看著他那副德行,撇了撇嘴,站起身,拍了拍手上的点心渣。
“看来是谈不拢了。浪费时间。”
说完,她头也不回地走了,留下李德福一个人在风中凌乱,气得浑身发抖。
张姜这边刚走,一名小太监就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,哭丧著脸稟报。
“乾爹!那……那个破虏校尉吕方明,他……他拒不见您!”
“什么?!”
“他派亲卫回话,说……说將军令他操练兵马,军务在身,不敢与天使閒谈,怕误了军机!”
误了军机!
好一个误了军机!
这已经不是打脸了,这是指著鼻子骂他李德福一个太监,瞎掺和军国大事!
“反了!都反了!!”
李德福再也绷不住了,一把將桌上的名贵茶具全都扫落在地,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。
离间计,彻底破產!
“好!好一个陈远!你给咱家等著!”
李德福双眼血红,他知道,文的既然不行,那就只能来武的!
他猛地一拍桌子,对著门外尖叫道:“来人!传咱家將令!咱家要亲自巡查军备、清点粮册!咱家倒要看看,他陈远,拿什么来养这十万大军!”
这一次,陈远答应得比上次还痛快。
“公公一心为国,本將岂有不从之理?王朗!”
老管家王朗再次应声而出,脸上掛著忠厚老实的笑容:“將军,老奴在。”
“全力配合钦差大人!大人想看什么,就看什么!想查什么,就查什么!不得有误!”
“老奴……遵命!”
接下来的三天,成了李德福这辈子最大的噩梦。
王朗带著他去看帐本。
“哎呀!公公您瞧,这……这也不知哪来的耗子,把去年的帐本给啃了!罪过,罪过啊!”
王朗指著一堆碎纸屑,痛心疾首。
李德福去看粮仓。
“公公!真不巧!管仓库钥匙的那个兄弟,昨天喝多了,掉茅坑里了,钥匙……也跟著掉下去了!这会儿正叫人捞呢!”
王朗一脸的为难。
等好不容易找到备用钥匙,打开一座粮仓,里面空得能跑马。
“公公明鑑!这……这是咱们的疑兵之计!故意空出来的,就是为了迷惑戎狄探子!”
王朗说得头头是道,一脸“你真是个外行”的表情。
李德福被这老东西折腾得够呛,可人家理由编得圆,他连发火的由头都找不到!
而就在他被当猴耍得团团转的时候。
百里之外的鹤陟县,一线涧。
数千名振威营的士兵,和上万名自发前来的民夫,正热火朝天地吼著號子。
一车车由水泥被源源不断地浇筑进山体之中。
一座前所未见的雄关,在所有人的血汗浇灌下,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拔地而起!
第四天清晨。
李德福终於放弃了,他双眼布满血丝,整个人都瘦了一圈,失魂落魄地走在齐州城的街道上。
看著街道上车水马龙,百姓脸上洋溢著发自內心的笑容。
看著那些小贩和顾客,用军票交易时那份理所当然的信赖。
看著巡逻的士兵与百姓勾肩搭背,亲如一家……
一股寒意直窜头顶,凉透了骨头!
管理混乱?帐目不清?
放屁!
这分明是一种滴水不漏,配合默契到恐怖的阳谋!
他被耍了!从头到尾,他就像一个自作聪明的傻子,被陈远牵著鼻子,完美地避开了所有他想看到的东西!
“咕咚。”
李德福狠狠咽了口唾沫,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衣衫。
不能再待下去了!再待下去,自己这条命都得交代在这儿!
他当机立断,立刻返回郡守府,脸上立刻堆满了亲和的笑容,拉著陈远的手,亲热得像是见到了亲爹。
“陈將军!国之栋樑!国之栋樑啊!咱家这次回去,一定在陛下面前,为你好好请功!齐州军务安稳,百姓拥戴,咱家也该回京復命了!”
陈远看著他那拙劣的演技,同样笑得一脸真诚:“公公慢走,本將就不远送了。”
钦差仪仗,仓皇出城。
刚离开齐州地界,进入荒无人烟的山道。
李德福那张和善的脸,瞬间变得比恶鬼还要狰狞。
他猛地从袖中,掏出一只通体漆黑,眼神凶戾的信鸽。
飞快地在信管中塞入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。
扬手一挥,那只黑信鸽叫了一声,飞快地朝南边飞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