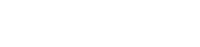乌云把月亮捂得严严实实,白云山寨里黑得像口封死的棺材。
此时的山寨,比那乱葬岗还热闹。
为了几袋子“官军遗落”的粟米。
过江龙手里的九环大刀都要砍卷刃了,对面穿山豹的人也没怂,拎著斧头互剁。
地上横七竖八躺著十几具尸首,血腥味混著汗臭,熏得人脑仁疼。
聚义厅內,独眼龙霸山恶一巴掌拍在紫檀木桌上,震得酒碗乱跳。
“反了!都他娘的反了!老子还没死呢,这帮兔崽子就开始分家產?”
他確实没死,但也就在这几个呼吸的事儿了。
两百步外的黑崖上,没有任何口令,只有机括咬合的轻微脆响。
五十具神臂弩平端著,铁矢在夜色里泛著哑光,冰冷得不讲道理。
领队的手往下一压。
嘣。
没有什么万箭齐发的呼啸,这种大杀器射出去的声音沉闷且短促。
霸山恶刚想再骂两句提提气,喉咙里突然卡出一声怪异的“咯咯”响。
他有些发懵地低下头,看著胸口凭空长出来的三截箭杆。
这玩意儿劲道大得离谱,直接贯穿了他的脖子、心口和肚子,把他整个人死死钉在了身后的虎皮交椅上。
血顺著箭杆往下淌,他想抬手,却发现力气正顺著那三个窟窿飞快流走。
直到咽气,这独眼龙都没明白,阎王爷怎么来得连个招呼都不打。
外头正杀得起劲的过江龙也没好到哪去。
他刚举起九环刀要给穿山豹开瓢,脑侧突然传来一声闷响,红的白的直接喷了穿山豹一脸。
穿山豹抹了一把脸上的温热,还没来得及庆幸,一支铁矢就从他后心穿过,把他钉在了泥地里。
“大当家没气了!”
“见鬼了!这箭哪来的!”
刚才还为了粮食拼命的匪徒们瞬间炸了窝,手里的兵器变得烫手,扔了一地。
这哪里是打仗,这分明是点名,谁冒头谁死。
“跑!快跑!是神臂弩!”
有人认出了这要命的傢伙,嗓子都喊劈了。
可惜,晚了。
“跑?往哪跑!”
黑暗中撞出一道人影,吕方明手里的百炼宝刀捲起一阵腥风,直接把一个想翻墙的小嘍囉劈成了两半。
他身上那套玄铁虎头甲还没沾血,但眼里的火都要喷出来了。
这半个月,他装孙子、扮草包,被人指著脊梁骨骂败军之將,这口恶气憋得他五臟六腑都在烧。
“都给老子把头抬起来!”
吕方明一脚踹翻个嚇破胆的匪徒,刀锋指著那群没头的苍蝇,吼声比雷还响:“看看老子是谁!看看老子是不是那个只会逃跑的草包!”
他身后的两千精锐如狼群下山,压抑许久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宣泄。这哪里是剿匪,这分明是一群受了委屈的野兽在撕咬猎物。
这不是打仗,是单方面的剁肉。
不到一个时辰,白云山寨静了下来。
除了偶尔响起的呻吟声和补刀的噗嗤声,再无半点反抗的动静。
吕方明一脚踹开聚义厅的大门,靴底踩著霸山恶还没干透的血,啐了一口。
“什么狗屁霸山恶,还没老子杀鸡费劲。”
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珠子,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歇口气,两个亲兵像拖死狗一样,拽著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扔了进来。
“校尉!这老小子躲在茅房后面的夹层里,身上穿著绸缎,不像个土匪,倒像个读书人。”
那中年人髮髻散乱,脸色煞白,下半身的绸裤湿了一大片,骚味直衝脑门。
一看到吕方明那身沾满碎肉的虎头甲,他哆嗦得像筛糠一样,脑门磕在青石板上砰砰作响。
“军爷饶命!军爷饶命啊!小人是被掳上山的肉票,也是个读圣贤书的,跟这帮贼寇不是一路人啊!”
吕方明皱了皱眉,用刀背挑起这人的下巴。
“肉票?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,养得比这山上的大当家还滋润。哪家的肉票还能在匪窝里长膘?”
他说著,手腕一翻,锋利的刀刃贴上了中年人的脖颈大动脉,冰凉的触感让对方瞬间翻起了白眼。
“老子最烦读书人满嘴跑马。既然不是一路人,那就送你上路,省得浪费粮食。”
“別!別杀我!我说!我是这山上的帐房!”
中年人尖叫著,声音都劈了叉,“我有用!我知道这寨子里的秘密!天大的秘密!”
吕方明手上的动作顿了顿,刀锋压出一道血痕:“最后一次机会,说不出点乾货,老子把你剁碎了餵狗。”
中年人咽了口唾沫,眼珠子乱转,最后像是豁出去了一般,瘫软在地上。
“这……这白云山的匪患,根本不是为了劫財。”
他喘著粗气,拋出了一个足以把天捅个窟窿的消息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背后真正的主子,不是北境商盟,也不是什么江湖草莽,而是……京城的平南侯!”
吕方明愣了一下,手里的刀差点没拿稳。
“你说谁?”
“平南侯!当朝一等侯爵!”
中年人哭丧著脸,竹筒倒豆子般全抖了出来,“侯爷每年都会派专人送来巨款,养著这几千號人。不为別的,就是为了让这白云山乱著!
“只要商路不通,北境就得一直乱,这样侯爷就能在朝堂上以『平乱』为名,年年伸手向户部要钱要粮!”
“这叫……养寇自重。”
轰!
这个名字,让吕方明如遭雷击,当场愣住。
他一把揪住那军师的衣领,整个人都懵了。
这已经不是剿匪了,这他娘的牵扯到京城里的侯爷,牵扯到朝堂之爭了!
这事儿他已经管不了了!
……
千里之外,京城临安。
金碧辉煌的紫宸殿內,薰香繚绕,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
新帝柴启那张尚带几分青涩的脸,此刻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微微扭曲。
他一把將手中的奏报狠狠砸在金砖地上,奏报的封皮上,赫然印著“北境急奏”四个大字。
“天火神雷?纸换金银?!”
柴启尖著嗓子,冷嘲热讽道,在空旷的大殿中迴荡不休,“一群边关的莽夫,仗著天高皇帝远,竟敢用这种荒天下之大谬的鬼话来糊弄朕!他们把朕当成了什么?三岁小儿吗?!”
殿下,文武百官噤若寒蝉,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只有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臣,颤巍巍地出列,躬身道:“陛下息怒。国库空虚,北境新胜之后,百废待兴,实不宜再动刀兵。依老臣愚见,那齐州陈远,或许是个人才。不如先行安抚,封官许愿,將其纳入朝廷掌控,再徐徐图之……”
“放屁!”
老臣话音未落,一名虎背熊腰,满脸络腮鬍的武將便踏前一步,声如洪钟:
“此等私印钱票,形同谋逆的乱臣贼子,今日不以雷霆之势剿灭,明日天下州府人人效仿,我大夏的江山,岂不是要处处称王?!”
“你……”老臣气得鬍子直抖。
“肃静!”柴启不耐烦地一挥蟒袍。
他看不起老臣的畏缩,也烦透了武將的咋呼。
他要的,是一个能让他彻底安心的法子。
就在这时,一个语气虽和缓,却听得人脊背发凉,慢悠悠地响了起来。
“陛下,两位大人所言,皆有道理。”
眾人循声望去,只见平南侯田左牧,一身锦绣朝服,缓步出列。
他生得相貌白净,看著文质彬彬,若非眼底深处偶尔闪过的一丝阴鷙,任谁都会以为他是个与世无爭的富贵閒人。
他先是对著老臣微微頷首,表示赞同:“王太傅所言极是,国库確实经不起折腾了。安抚,是上策。”
王太傅闻言,脸上露出一丝欣慰。
然而。
田左牧话锋一转,目光扫过那名武將,语气一沉,显得心事重重。
“但,张將军的顾虑,更是切中要害!那个陈远,绝非善类!”
他对著龙椅上的柴启,深深一揖,声音里演得一副忠心耿耿、忧心忡忡的模样。
“陛下,臣听闻,此人在齐州,以军票蛊惑军民,收拢人心。
“戎狄退兵,他便立刻吞併商盟,一夜之间,其聚敛的財富,怕是比我大夏一年的税收还要多!
“这等人物,野心之大,手段之狠,若不早日剪除,恐非北境之福,而是我大夏心腹之患啊!”
这番话,每一个字,都像一根毒针,精准地扎进了柴启內心最敏感、最恐惧的地方!
皇权旁落!
尾大不掉!
这四个字,像梦魘一样缠绕著这位根基不稳的年轻帝王。
田左牧这番话,完美地將陈远塑造成了一个潜伏的安禄山!
“那依爱卿之见,该当如何?”柴启的语气已经变得冰冷,看向北方的眼神里,杀机毕现。
田左牧悄悄弯了弯嘴角,没人察觉,他知道,计划得逞了。
“陛下,安抚的圣旨,要下!而且要大张旗鼓地下!封他个將军,赏他些金银,让他觉得朝廷软弱可欺,让他放鬆警惕!”
“然后,”他顿了顿,声音压得极低,透著股阴森森的寒意,“再派一名陛下最信得过的心腹,以钦差之名,前往齐州!明为巡查宣旨,实则,身负三重密令!”
“其一,摸清他陈远的家底,看他到底有多少兵,多少钱!”
“其二,宣读圣旨时,看他態度如何。若他倨傲不恭,便以此为由,当场发难!同时,私下接触其部將,许以高官厚禄,行分化瓦解之策!”
“其三!”田左牧的声音陡然变得狠厉,“命三万京营精锐,秘密南下,陈兵於齐州南方的门户——鹤陟县!一旦那陈远有半点不臣之心,钦差一声令下,大军即刻奇袭鹤陟!断其后路,將其活活困死在齐州!”
好一招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!
好一招“先礼后兵,图穷匕见”!
柴启的眼睛,瞬间亮了!
他仿佛已经看到,那个叫陈远的跳樑小丑,在自己这套天衣无缝的连环计下,跪地求饶的悽惨模样。
“好!好一个平南侯!”
柴启龙顏大悦,一巴掌拍在龙椅扶手上,“就依爱卿所言!即刻擬旨!”
他扫视全场,目光最终落在了自己的亲信,內廷卫指挥使——李德福的身上。
“李德福,就由你,代朕走这一趟!”
“老奴……遵旨!”
一个面白无须,眼神阴沉锐利的太监,悄无声息地出列,领下了这道杀机四伏的密令。
大殿之內,君臣自以为定下千古妙计,气氛重新变得祥和。
他们谁也不知道。
其实在实力面前,一切阴谋诡计都是虚无。
……
齐州,郡守府。
书房內,陈远的手指,正轻轻摩挲著一张字跡潦草的供状。
正是吕方明从白云山八百里加急送回来的,那名匪寨军师的亲笔画押。
看著供状末尾,“京城平南侯”那几个字,陈远冷笑了一声,眼里透著寒意。
他之前的种种猜测,在这一刻,被彻底证实。
北境商盟,不过是推到台前的傀儡。
白云山匪患,也只是別人棋盘上的一颗閒子。
真正想让北境一直乱下去,想靠著战乱来攫取权力和財富的毒蛇,一直盘踞在千里之外的临安城。
“可惜,我来了。”
陈远轻声自语,將那张供状凑到烛火前,看著它化为一捧飞灰。
他正思索著,该如何利用这颗意外挖出来的棋子,好好跟那位素未谋面的侯爷下一盘大棋时。
“砰!”
书房的门,被人风风火火地撞开。
“陈远!別琢磨你那些弯弯绕绕了,你的『大麻烦』,自己送上门了!”
不用回头,陈远都知道来人是冯四娘。
也只有她,敢这么不敲门就闯进来。
他转过头,只见冯四娘和程若雪二人並肩而入。
两人的脸上,都带著一丝如出一辙的凝重与讥讽。
程若雪更是“啪”的一声,將一封盖著火漆印的加急军报,拍在了陈远面前的桌子上。
“齐州边境的斥候刚传回来的消息。”
程若雪指了指那份军报,嘴角带著一丝冷笑,“一支打著皇家仪仗的队伍,正朝咱们这儿来。领头的,是个太监,自称是临安城来的钦差大臣。”
她顿了顿,一字一句地说道:
“指名道姓,要你这个『齐州守將』,出城三十里,跪接圣旨呢!”
书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
张姜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,眉尖微不可查地蹙了一下。
冯四娘更是直接骂出了声:“他娘的!咱们在这儿跟人拼死拼活,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安生日子,京城里那帮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,倒会摘桃子了!还跪接?接他娘的腿!”
此时的山寨,比那乱葬岗还热闹。
为了几袋子“官军遗落”的粟米。
过江龙手里的九环大刀都要砍卷刃了,对面穿山豹的人也没怂,拎著斧头互剁。
地上横七竖八躺著十几具尸首,血腥味混著汗臭,熏得人脑仁疼。
聚义厅內,独眼龙霸山恶一巴掌拍在紫檀木桌上,震得酒碗乱跳。
“反了!都他娘的反了!老子还没死呢,这帮兔崽子就开始分家產?”
他確实没死,但也就在这几个呼吸的事儿了。
两百步外的黑崖上,没有任何口令,只有机括咬合的轻微脆响。
五十具神臂弩平端著,铁矢在夜色里泛著哑光,冰冷得不讲道理。
领队的手往下一压。
嘣。
没有什么万箭齐发的呼啸,这种大杀器射出去的声音沉闷且短促。
霸山恶刚想再骂两句提提气,喉咙里突然卡出一声怪异的“咯咯”响。
他有些发懵地低下头,看著胸口凭空长出来的三截箭杆。
这玩意儿劲道大得离谱,直接贯穿了他的脖子、心口和肚子,把他整个人死死钉在了身后的虎皮交椅上。
血顺著箭杆往下淌,他想抬手,却发现力气正顺著那三个窟窿飞快流走。
直到咽气,这独眼龙都没明白,阎王爷怎么来得连个招呼都不打。
外头正杀得起劲的过江龙也没好到哪去。
他刚举起九环刀要给穿山豹开瓢,脑侧突然传来一声闷响,红的白的直接喷了穿山豹一脸。
穿山豹抹了一把脸上的温热,还没来得及庆幸,一支铁矢就从他后心穿过,把他钉在了泥地里。
“大当家没气了!”
“见鬼了!这箭哪来的!”
刚才还为了粮食拼命的匪徒们瞬间炸了窝,手里的兵器变得烫手,扔了一地。
这哪里是打仗,这分明是点名,谁冒头谁死。
“跑!快跑!是神臂弩!”
有人认出了这要命的傢伙,嗓子都喊劈了。
可惜,晚了。
“跑?往哪跑!”
黑暗中撞出一道人影,吕方明手里的百炼宝刀捲起一阵腥风,直接把一个想翻墙的小嘍囉劈成了两半。
他身上那套玄铁虎头甲还没沾血,但眼里的火都要喷出来了。
这半个月,他装孙子、扮草包,被人指著脊梁骨骂败军之將,这口恶气憋得他五臟六腑都在烧。
“都给老子把头抬起来!”
吕方明一脚踹翻个嚇破胆的匪徒,刀锋指著那群没头的苍蝇,吼声比雷还响:“看看老子是谁!看看老子是不是那个只会逃跑的草包!”
他身后的两千精锐如狼群下山,压抑许久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宣泄。这哪里是剿匪,这分明是一群受了委屈的野兽在撕咬猎物。
这不是打仗,是单方面的剁肉。
不到一个时辰,白云山寨静了下来。
除了偶尔响起的呻吟声和补刀的噗嗤声,再无半点反抗的动静。
吕方明一脚踹开聚义厅的大门,靴底踩著霸山恶还没干透的血,啐了一口。
“什么狗屁霸山恶,还没老子杀鸡费劲。”
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珠子,正想找个地方坐下歇口气,两个亲兵像拖死狗一样,拽著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扔了进来。
“校尉!这老小子躲在茅房后面的夹层里,身上穿著绸缎,不像个土匪,倒像个读书人。”
那中年人髮髻散乱,脸色煞白,下半身的绸裤湿了一大片,骚味直衝脑门。
一看到吕方明那身沾满碎肉的虎头甲,他哆嗦得像筛糠一样,脑门磕在青石板上砰砰作响。
“军爷饶命!军爷饶命啊!小人是被掳上山的肉票,也是个读圣贤书的,跟这帮贼寇不是一路人啊!”
吕方明皱了皱眉,用刀背挑起这人的下巴。
“肉票?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,养得比这山上的大当家还滋润。哪家的肉票还能在匪窝里长膘?”
他说著,手腕一翻,锋利的刀刃贴上了中年人的脖颈大动脉,冰凉的触感让对方瞬间翻起了白眼。
“老子最烦读书人满嘴跑马。既然不是一路人,那就送你上路,省得浪费粮食。”
“別!別杀我!我说!我是这山上的帐房!”
中年人尖叫著,声音都劈了叉,“我有用!我知道这寨子里的秘密!天大的秘密!”
吕方明手上的动作顿了顿,刀锋压出一道血痕:“最后一次机会,说不出点乾货,老子把你剁碎了餵狗。”
中年人咽了口唾沫,眼珠子乱转,最后像是豁出去了一般,瘫软在地上。
“这……这白云山的匪患,根本不是为了劫財。”
他喘著粗气,拋出了一个足以把天捅个窟窿的消息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背后真正的主子,不是北境商盟,也不是什么江湖草莽,而是……京城的平南侯!”
吕方明愣了一下,手里的刀差点没拿稳。
“你说谁?”
“平南侯!当朝一等侯爵!”
中年人哭丧著脸,竹筒倒豆子般全抖了出来,“侯爷每年都会派专人送来巨款,养著这几千號人。不为別的,就是为了让这白云山乱著!
“只要商路不通,北境就得一直乱,这样侯爷就能在朝堂上以『平乱』为名,年年伸手向户部要钱要粮!”
“这叫……养寇自重。”
轰!
这个名字,让吕方明如遭雷击,当场愣住。
他一把揪住那军师的衣领,整个人都懵了。
这已经不是剿匪了,这他娘的牵扯到京城里的侯爷,牵扯到朝堂之爭了!
这事儿他已经管不了了!
……
千里之外,京城临安。
金碧辉煌的紫宸殿內,薰香繚绕,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
新帝柴启那张尚带几分青涩的脸,此刻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微微扭曲。
他一把將手中的奏报狠狠砸在金砖地上,奏报的封皮上,赫然印著“北境急奏”四个大字。
“天火神雷?纸换金银?!”
柴启尖著嗓子,冷嘲热讽道,在空旷的大殿中迴荡不休,“一群边关的莽夫,仗著天高皇帝远,竟敢用这种荒天下之大谬的鬼话来糊弄朕!他们把朕当成了什么?三岁小儿吗?!”
殿下,文武百官噤若寒蝉,连呼吸都放轻了。
只有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臣,颤巍巍地出列,躬身道:“陛下息怒。国库空虚,北境新胜之后,百废待兴,实不宜再动刀兵。依老臣愚见,那齐州陈远,或许是个人才。不如先行安抚,封官许愿,將其纳入朝廷掌控,再徐徐图之……”
“放屁!”
老臣话音未落,一名虎背熊腰,满脸络腮鬍的武將便踏前一步,声如洪钟:
“此等私印钱票,形同谋逆的乱臣贼子,今日不以雷霆之势剿灭,明日天下州府人人效仿,我大夏的江山,岂不是要处处称王?!”
“你……”老臣气得鬍子直抖。
“肃静!”柴启不耐烦地一挥蟒袍。
他看不起老臣的畏缩,也烦透了武將的咋呼。
他要的,是一个能让他彻底安心的法子。
就在这时,一个语气虽和缓,却听得人脊背发凉,慢悠悠地响了起来。
“陛下,两位大人所言,皆有道理。”
眾人循声望去,只见平南侯田左牧,一身锦绣朝服,缓步出列。
他生得相貌白净,看著文质彬彬,若非眼底深处偶尔闪过的一丝阴鷙,任谁都会以为他是个与世无爭的富贵閒人。
他先是对著老臣微微頷首,表示赞同:“王太傅所言极是,国库確实经不起折腾了。安抚,是上策。”
王太傅闻言,脸上露出一丝欣慰。
然而。
田左牧话锋一转,目光扫过那名武將,语气一沉,显得心事重重。
“但,张將军的顾虑,更是切中要害!那个陈远,绝非善类!”
他对著龙椅上的柴启,深深一揖,声音里演得一副忠心耿耿、忧心忡忡的模样。
“陛下,臣听闻,此人在齐州,以军票蛊惑军民,收拢人心。
“戎狄退兵,他便立刻吞併商盟,一夜之间,其聚敛的財富,怕是比我大夏一年的税收还要多!
“这等人物,野心之大,手段之狠,若不早日剪除,恐非北境之福,而是我大夏心腹之患啊!”
这番话,每一个字,都像一根毒针,精准地扎进了柴启內心最敏感、最恐惧的地方!
皇权旁落!
尾大不掉!
这四个字,像梦魘一样缠绕著这位根基不稳的年轻帝王。
田左牧这番话,完美地將陈远塑造成了一个潜伏的安禄山!
“那依爱卿之见,该当如何?”柴启的语气已经变得冰冷,看向北方的眼神里,杀机毕现。
田左牧悄悄弯了弯嘴角,没人察觉,他知道,计划得逞了。
“陛下,安抚的圣旨,要下!而且要大张旗鼓地下!封他个將军,赏他些金银,让他觉得朝廷软弱可欺,让他放鬆警惕!”
“然后,”他顿了顿,声音压得极低,透著股阴森森的寒意,“再派一名陛下最信得过的心腹,以钦差之名,前往齐州!明为巡查宣旨,实则,身负三重密令!”
“其一,摸清他陈远的家底,看他到底有多少兵,多少钱!”
“其二,宣读圣旨时,看他態度如何。若他倨傲不恭,便以此为由,当场发难!同时,私下接触其部將,许以高官厚禄,行分化瓦解之策!”
“其三!”田左牧的声音陡然变得狠厉,“命三万京营精锐,秘密南下,陈兵於齐州南方的门户——鹤陟县!一旦那陈远有半点不臣之心,钦差一声令下,大军即刻奇袭鹤陟!断其后路,將其活活困死在齐州!”
好一招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!
好一招“先礼后兵,图穷匕见”!
柴启的眼睛,瞬间亮了!
他仿佛已经看到,那个叫陈远的跳樑小丑,在自己这套天衣无缝的连环计下,跪地求饶的悽惨模样。
“好!好一个平南侯!”
柴启龙顏大悦,一巴掌拍在龙椅扶手上,“就依爱卿所言!即刻擬旨!”
他扫视全场,目光最终落在了自己的亲信,內廷卫指挥使——李德福的身上。
“李德福,就由你,代朕走这一趟!”
“老奴……遵旨!”
一个面白无须,眼神阴沉锐利的太监,悄无声息地出列,领下了这道杀机四伏的密令。
大殿之內,君臣自以为定下千古妙计,气氛重新变得祥和。
他们谁也不知道。
其实在实力面前,一切阴谋诡计都是虚无。
……
齐州,郡守府。
书房內,陈远的手指,正轻轻摩挲著一张字跡潦草的供状。
正是吕方明从白云山八百里加急送回来的,那名匪寨军师的亲笔画押。
看著供状末尾,“京城平南侯”那几个字,陈远冷笑了一声,眼里透著寒意。
他之前的种种猜测,在这一刻,被彻底证实。
北境商盟,不过是推到台前的傀儡。
白云山匪患,也只是別人棋盘上的一颗閒子。
真正想让北境一直乱下去,想靠著战乱来攫取权力和財富的毒蛇,一直盘踞在千里之外的临安城。
“可惜,我来了。”
陈远轻声自语,將那张供状凑到烛火前,看著它化为一捧飞灰。
他正思索著,该如何利用这颗意外挖出来的棋子,好好跟那位素未谋面的侯爷下一盘大棋时。
“砰!”
书房的门,被人风风火火地撞开。
“陈远!別琢磨你那些弯弯绕绕了,你的『大麻烦』,自己送上门了!”
不用回头,陈远都知道来人是冯四娘。
也只有她,敢这么不敲门就闯进来。
他转过头,只见冯四娘和程若雪二人並肩而入。
两人的脸上,都带著一丝如出一辙的凝重与讥讽。
程若雪更是“啪”的一声,將一封盖著火漆印的加急军报,拍在了陈远面前的桌子上。
“齐州边境的斥候刚传回来的消息。”
程若雪指了指那份军报,嘴角带著一丝冷笑,“一支打著皇家仪仗的队伍,正朝咱们这儿来。领头的,是个太监,自称是临安城来的钦差大臣。”
她顿了顿,一字一句地说道:
“指名道姓,要你这个『齐州守將』,出城三十里,跪接圣旨呢!”
书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
张姜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,眉尖微不可查地蹙了一下。
冯四娘更是直接骂出了声:“他娘的!咱们在这儿跟人拼死拼活,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安生日子,京城里那帮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,倒会摘桃子了!还跪接?接他娘的腿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