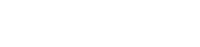唐玉在茶房里听得心惊肉跳。
当杨令薇说出“丫鬟病死、並非虐杀”时,她心头猛地一沉。
外头又何曾有过这般確切的传闻?
没人传的事,可她今日为何主动提起?
电光石火间,一个念头窜进唐玉脑中。
她是在堵嘴!
先用一桩相对可控的错事认下来,再给它安上一个情有可原的结局。
如此,日后若真有人拿此事攻訐,她便可理直气壮地辩白:
“我早已向侯府坦白,是病故,何来虐杀?”
至於真相如何,反倒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,她抢先一步,在听者心里埋下了她是被冤枉的种子。
这心思……何其縝密,又何其可怖。
用主动“认小过”,来防备日后被揭“大恶”。
老夫人听到这里,面色已然变得十分难看。
无论是“失手伤姐”还是“丫鬟恶疾病逝”牵扯出虐杀传闻。
都绝非什么光彩之事,桩桩件件都透著內宅阴私与不祥。
孟氏却仍端得住,只淡淡道:
“外头这些捕风捉影、以讹传讹的言语,我侯府內宅之人,倒未曾听闻。”
“不过,既是无稽之谈,杨四小姐也不必过於掛怀。”
“公道自在人心,清者自清。没做过的事,上天不会降罪,你但且安心便是。”
这话听著是安抚,实则撇清了侯府与流言的关係。
也並未对杨令薇的说法全盘採信,只给了个不痛不痒的“清者自清”。
孟氏说完,目光转向老夫人,似在请示。
老夫人却没看孟氏,而是將目光重新投向跪在地上的杨令薇。
她捻著佛珠,沉声问道:
“那你说,你的第三件错事,又是什么?”
杨令薇身体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,仿佛鼓足了极大的勇气,才哽咽著开口,声音里充满了悔恨与羞惭:
“这第三件……是前日,在贵府的插花宴上……”
她抬起泪眼,神情悲伤欲绝,
“令薇因一己私心,妒忌心起,言行无状……因听闻、因介意二爷从前……曾纳过一位房里人……”
“心中不平,竟在言语间……不慎衝撞、冒犯了二爷……”
“回去之后,令薇日夜难安,如坠冰窟,深觉自己品行有亏,愧对父母教养,更无顏面对侯府长辈……特来请罪!”
茶房里,唐玉呼吸一窒。
她说的是紫藤架下的事!
却將羞辱威胁她,轻描淡写成了衝撞二爷。
如此一来,在老夫人与孟氏听来,便只是未来儿媳因儿子旧事拈酸吃醋,闹了点小性子。
唐玉心中惴惴。
今日的杨令薇虽说是自陈罪状,不过依她所见,杨令薇掩盖了最严重的那一桩罪责。
即买凶杀人。
前面两桩,“伤害亲姐”、“虐杀奴僕”。
因是在杨家发生的事,侯府也没有確凿证据去查证,任由杨令薇去说也就罢了。
可买凶杀人,这可是明明白白地犯了刑罚的凶罪。
更別说侯府中人知晓、参与了此事,对那凶手同仇敌愾。
若杨令薇真將买凶杀人一事说出来,第一个就要起厌恶之心的,就是老夫人。
到那时,她又怎可能进得了侯府的门?
江凌川那晚在她房中,確定地说过,买凶杀她之人,与杨家有联繫。
这和她自己之前的猜测完全吻合。
若杨令薇今日真是来认错、退婚,祈求宽恕。
为何对“买凶杀人”这等十恶不赦的大罪只字不提。
反而只揪著妒忌、言语衝撞这些后宅女子相对较轻的错处大做文章?
这哪里是认错?
分明是以退为进。
用“善妒”“衝动”这些后宅女子的小错,来遮掩真正十恶不赦的大罪,博取同情,试图矇混过关。
果然,老夫人听完这“第三错”,脸色虽然依旧难看,但並未变得更加铁青。
似乎觉得这妒忌、衝撞虽不妥,但比起前两桩涉及“伤害亲姐”、“人命官司”的传闻,反而显得平常。
孟氏则坐直了身子,肃容道:
“杨四小姐,你既知『妒』乃女子大忌,为贤妇者,当以平和自若、不妒不燥为要。”
“你如今……毕竟尚未入我侯府之门,这些闺阁修身之道,本该由你母亲严加教导。”
她顿了顿,语气稍微缓和,但依旧带著疏离:
“不过,你既已知错,肯来当面懺悔,倒也不算无药可救。”
“能自省,便是幸事一桩。日后还当时时谨记,克己復礼才是。”
杨令薇微微抬眼,看向上首的老夫人和大夫人。
她看老夫人的脸色虽然难看,但不至於色变。
看孟氏的脸虽然严肃,但看向她的眼中仍是安抚,心中稍定,
赌对了。
只要错处仍在可谅解的范畴內,便有转圜余地。
她立刻以额触地,深深地跪伏下去,磕头声清晰可闻,哭得声噎气堵:
“令薇不敢奢求老祖宗、夫人原谅……令薇自知罪孽深重,万死难辞其咎……”
“今日斗胆前来,並非为了求得宽恕,只是、只是心中煎熬,日夜难安。”
“若再不將这一切坦白说出,怕是、怕是要被这愧疚活活折磨致死……”
她抬起头,泪流满面,精心描画的妆容早已被泪水冲刷得狼藉不堪。
髮髻鬆散,几缕湿发狼狈地贴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。
眼神里充满了悔恨与绝望,仿佛一个即將溺毙之人,抓住最后一根浮木:
“说出来……哪怕立刻被赶出去,哪怕被天下人唾弃,令薇也认了!”
“只求……只求能得一刻心安,能稍稍偿还这滔天罪孽於万一……”
说罢,她再次近乎自虐般地以头抢地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瘦弱的肩膀因剧烈的抽泣而不断颤抖。
整个人蜷缩在地上,像一片秋风里即將零落的枯叶,淒楚可怜到了极点。
老夫人看著她这副全然崩溃、自轻自贱到泥土里的模样。
饶是心中对她所言的几桩事仍有疑虑和不满,此刻也难免生出几分不忍。
到底是看著长大的世交之女,如此卑微哀恳,哭求的只是一个“心安”……
老夫人眉头深锁,捻动佛珠的手指停了下来。
嘴唇微微翕动,看著地上那个颤抖的身影,准备开口让丫鬟先將她搀扶起来。
然而,就在老夫人开口之际,
“报——”
门口通传丫鬟急促的声音突兀响起。
几乎与这声音同时。
一只黑色皂靴,悍然踏入正厅门槛。
来人身姿挺拔高大,逆著门外天光,带来一股凛冽煞气。
他目光如电,冷冷地扫过跪在地上,惊恐抬头望来的杨令薇。
俊美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,唯有眼底凝结著万年寒冰。
正是江凌川。
江凌川甚至没有向老夫人和孟氏行礼。
只径直走到杨令薇身前几步处,居高临下地睥睨著她。
片刻之后,男人开口,薄唇微启,声音冷凝,字字凿心:
“杨家小姐真是……巧舌如簧,辩才无碍。”
“既然你这般『坦诚』,爷也问你两桩事。”
他微微俯身,盯著杨令薇骤然惨白的脸:
“三月十七,你遣丫鬟丁香,经外院僕役杨大之手,於城西醉仙居雅间,付给绰號过山风的亡命徒纹银一百两——所为何事?”
“三月廿二,你又命松涛庄管事,从你私帐支取黄金一百两,经三道中间人,匯入漕帮快刀刘的秘密户头——这钱,又是用作何处?”
“不如,你將这两桩小事,也坦诚说与大家听听?”
当杨令薇说出“丫鬟病死、並非虐杀”时,她心头猛地一沉。
外头又何曾有过这般確切的传闻?
没人传的事,可她今日为何主动提起?
电光石火间,一个念头窜进唐玉脑中。
她是在堵嘴!
先用一桩相对可控的错事认下来,再给它安上一个情有可原的结局。
如此,日后若真有人拿此事攻訐,她便可理直气壮地辩白:
“我早已向侯府坦白,是病故,何来虐杀?”
至於真相如何,反倒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,她抢先一步,在听者心里埋下了她是被冤枉的种子。
这心思……何其縝密,又何其可怖。
用主动“认小过”,来防备日后被揭“大恶”。
老夫人听到这里,面色已然变得十分难看。
无论是“失手伤姐”还是“丫鬟恶疾病逝”牵扯出虐杀传闻。
都绝非什么光彩之事,桩桩件件都透著內宅阴私与不祥。
孟氏却仍端得住,只淡淡道:
“外头这些捕风捉影、以讹传讹的言语,我侯府內宅之人,倒未曾听闻。”
“不过,既是无稽之谈,杨四小姐也不必过於掛怀。”
“公道自在人心,清者自清。没做过的事,上天不会降罪,你但且安心便是。”
这话听著是安抚,实则撇清了侯府与流言的关係。
也並未对杨令薇的说法全盘採信,只给了个不痛不痒的“清者自清”。
孟氏说完,目光转向老夫人,似在请示。
老夫人却没看孟氏,而是將目光重新投向跪在地上的杨令薇。
她捻著佛珠,沉声问道:
“那你说,你的第三件错事,又是什么?”
杨令薇身体几不可察地颤了一下,仿佛鼓足了极大的勇气,才哽咽著开口,声音里充满了悔恨与羞惭:
“这第三件……是前日,在贵府的插花宴上……”
她抬起泪眼,神情悲伤欲绝,
“令薇因一己私心,妒忌心起,言行无状……因听闻、因介意二爷从前……曾纳过一位房里人……”
“心中不平,竟在言语间……不慎衝撞、冒犯了二爷……”
“回去之后,令薇日夜难安,如坠冰窟,深觉自己品行有亏,愧对父母教养,更无顏面对侯府长辈……特来请罪!”
茶房里,唐玉呼吸一窒。
她说的是紫藤架下的事!
却將羞辱威胁她,轻描淡写成了衝撞二爷。
如此一来,在老夫人与孟氏听来,便只是未来儿媳因儿子旧事拈酸吃醋,闹了点小性子。
唐玉心中惴惴。
今日的杨令薇虽说是自陈罪状,不过依她所见,杨令薇掩盖了最严重的那一桩罪责。
即买凶杀人。
前面两桩,“伤害亲姐”、“虐杀奴僕”。
因是在杨家发生的事,侯府也没有確凿证据去查证,任由杨令薇去说也就罢了。
可买凶杀人,这可是明明白白地犯了刑罚的凶罪。
更別说侯府中人知晓、参与了此事,对那凶手同仇敌愾。
若杨令薇真將买凶杀人一事说出来,第一个就要起厌恶之心的,就是老夫人。
到那时,她又怎可能进得了侯府的门?
江凌川那晚在她房中,確定地说过,买凶杀她之人,与杨家有联繫。
这和她自己之前的猜测完全吻合。
若杨令薇今日真是来认错、退婚,祈求宽恕。
为何对“买凶杀人”这等十恶不赦的大罪只字不提。
反而只揪著妒忌、言语衝撞这些后宅女子相对较轻的错处大做文章?
这哪里是认错?
分明是以退为进。
用“善妒”“衝动”这些后宅女子的小错,来遮掩真正十恶不赦的大罪,博取同情,试图矇混过关。
果然,老夫人听完这“第三错”,脸色虽然依旧难看,但並未变得更加铁青。
似乎觉得这妒忌、衝撞虽不妥,但比起前两桩涉及“伤害亲姐”、“人命官司”的传闻,反而显得平常。
孟氏则坐直了身子,肃容道:
“杨四小姐,你既知『妒』乃女子大忌,为贤妇者,当以平和自若、不妒不燥为要。”
“你如今……毕竟尚未入我侯府之门,这些闺阁修身之道,本该由你母亲严加教导。”
她顿了顿,语气稍微缓和,但依旧带著疏离:
“不过,你既已知错,肯来当面懺悔,倒也不算无药可救。”
“能自省,便是幸事一桩。日后还当时时谨记,克己復礼才是。”
杨令薇微微抬眼,看向上首的老夫人和大夫人。
她看老夫人的脸色虽然难看,但不至於色变。
看孟氏的脸虽然严肃,但看向她的眼中仍是安抚,心中稍定,
赌对了。
只要错处仍在可谅解的范畴內,便有转圜余地。
她立刻以额触地,深深地跪伏下去,磕头声清晰可闻,哭得声噎气堵:
“令薇不敢奢求老祖宗、夫人原谅……令薇自知罪孽深重,万死难辞其咎……”
“今日斗胆前来,並非为了求得宽恕,只是、只是心中煎熬,日夜难安。”
“若再不將这一切坦白说出,怕是、怕是要被这愧疚活活折磨致死……”
她抬起头,泪流满面,精心描画的妆容早已被泪水冲刷得狼藉不堪。
髮髻鬆散,几缕湿发狼狈地贴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。
眼神里充满了悔恨与绝望,仿佛一个即將溺毙之人,抓住最后一根浮木:
“说出来……哪怕立刻被赶出去,哪怕被天下人唾弃,令薇也认了!”
“只求……只求能得一刻心安,能稍稍偿还这滔天罪孽於万一……”
说罢,她再次近乎自虐般地以头抢地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
瘦弱的肩膀因剧烈的抽泣而不断颤抖。
整个人蜷缩在地上,像一片秋风里即將零落的枯叶,淒楚可怜到了极点。
老夫人看著她这副全然崩溃、自轻自贱到泥土里的模样。
饶是心中对她所言的几桩事仍有疑虑和不满,此刻也难免生出几分不忍。
到底是看著长大的世交之女,如此卑微哀恳,哭求的只是一个“心安”……
老夫人眉头深锁,捻动佛珠的手指停了下来。
嘴唇微微翕动,看著地上那个颤抖的身影,准备开口让丫鬟先將她搀扶起来。
然而,就在老夫人开口之际,
“报——”
门口通传丫鬟急促的声音突兀响起。
几乎与这声音同时。
一只黑色皂靴,悍然踏入正厅门槛。
来人身姿挺拔高大,逆著门外天光,带来一股凛冽煞气。
他目光如电,冷冷地扫过跪在地上,惊恐抬头望来的杨令薇。
俊美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,唯有眼底凝结著万年寒冰。
正是江凌川。
江凌川甚至没有向老夫人和孟氏行礼。
只径直走到杨令薇身前几步处,居高临下地睥睨著她。
片刻之后,男人开口,薄唇微启,声音冷凝,字字凿心:
“杨家小姐真是……巧舌如簧,辩才无碍。”
“既然你这般『坦诚』,爷也问你两桩事。”
他微微俯身,盯著杨令薇骤然惨白的脸:
“三月十七,你遣丫鬟丁香,经外院僕役杨大之手,於城西醉仙居雅间,付给绰號过山风的亡命徒纹银一百两——所为何事?”
“三月廿二,你又命松涛庄管事,从你私帐支取黄金一百两,经三道中间人,匯入漕帮快刀刘的秘密户头——这钱,又是用作何处?”
“不如,你將这两桩小事,也坦诚说与大家听听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