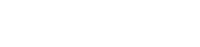第638章 坐望(二)
四月十二日(1645年6月8日),长江口的风带著咸腥水气,刮过南沙镇(今崇明岛新河镇)外那片沿著江岸绵延数里的难民营地。
天刚蒙蒙亮,陈阿婆就佝僂著身子钻进芦苇盪,枯瘦的手指在泥泞里摸索,指甲缝里嵌满黑泥,半天才能扯出几根还算完整的芦苇根。
这些带著泥土的根茎,待会要在江水里反覆漂洗,才能下锅熬煮。
她的小孙子狗剩蹲在窝棚口,怀里抱著个豁了口的陶碗,碗沿还沾著昨天的粥渍,一双大眼睛直勾勾盯著不远处沈家粥棚的方向,喉咙里不时发出细碎的吞咽声。
窝棚是用芦苇杆和茅草搭的,顶上盖著几片破旧的油布。
昨夜下了场小雨,棚角还在滴水,地上铺著的乾草湿了大半,散发出浓重的霉味。
这样的棲身之所,在营地里隨处可见。
一万二千余难民挤在这片临江的滩涂上,密密麻麻的木屋歪扭著,橡子都是捡来的废木,有的乾脆用绳索捆著芦苇当墙。
更为简陋的,乾脆把茅草堆成穹顶,江风掠过时,整个棚顶都在晃动,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。
面容枯槁的难民们在晨雾中往来穿梭,有的背著破麻袋四处捡拾能烧的芦苇和浮木,有的围在营地边缘的江水边淘洗野菜,浑浊的江水里飘著几片菜叶。
一个妇人弯腰搓洗衣物时,后腰的补丁裂开个口子,露出里面乾瘦的皮肤。
偶尔有孩童的哭闹声被江涛吞没,隨即又响起妇人沙哑的哄劝。
营地西头传来一阵阵咳嗽声,一群河南来的难民正围著个老郎中,他手里捏著几根草药,摇头嘆道:“这是风寒入体,得有薑汤发汗才行。可这营地里,哪来寻的到生薑.————
”
“阿婆,今天能喝上稠点的粥吗?“狗剩的声音带著怯生生的期盼,小手上还沾著窝棚里的草屑。
阿婆將拾来的柴草拢好,拍了拍沾在衣襟上的泥点,目光落在远处粥棚前那面绣著“沈“字的蓝色旗帜上:“能,沈家老爷心善,还有新华来的先生们送粮,饿不死咱们。”
她的话音刚落,就见几个穿著青色短褂、腰系黑布带的汉子推著独轮车走来。
车軲轆碾过泥地发出“吱呀“声响,车上的木桶冒著热气裹挟著米香,瞬间点燃了人群的期待。
人群立刻骚动起来,捧著各式各样的容器围过去,有豁口的陶碗,有开裂的木盆,甚至还有大片荷叶捲起来的临时容器。
儘管,所有人早已飢肠轆轆,但没人敢插队。
维持秩序的沈府家丁腰挎短刀,眼神凶狠地扫过人群。
领头的家丁叫沈忠,是沈家船工的后代,胳膊上有常年摇櫓磨出的厚茧,见有人往前挤,立即沉喝道:“都排好队!沈老爷说了,人人有份!谁敢乱来,就取消今日份例!
66
人群霎时安静下来,只剩下木勺刮过桶底的沙沙声。
更远处的哨卡旁,几个新华武装民兵正倚在寨墙上休息,他们穿著灰色號衣(军装),手中端著火统,一脸戚戚地望著这边。
南沙镇东头的沈府,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青瓦粉墙的宅院连绵数亩,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威风凛凛,门楣上掛著“资善堂“的匾额,那是万历年间某位致仕阁老亲赐的。
专用码头停靠著十余艘高大的沙船,船身漆成深褐色,船头雕刻的虎头在晨光中栩棚如生。
船帆卷在桅杆上,“沈氏船行“四个大字隱约可见,脚夫们正扛著粮袋往返於仓库之间,沉重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迴荡。
花厅內,年过花甲的老太爷沈墉靠在太师椅上,椅子是酸枝木做的,扶手处雕著缠枝莲纹样,他手里捏著一串翡翠佛珠,每颗珠子都温润通透。
对面坐著的沈廷扬一身青色官袍,补子上的鷺鷥纹样显示著他国子监司业的身份。
他前几日才从淮安乘船回来,脸上还带著旅途的风尘,鬢角沾著些许江雾凝成的水珠。
一套景德镇青花茶具摆在桌上,茶烟裊裊,龙井的清香在室內瀰漫。
“廷扬,难民营中的存粮还能支撑多久?“沈墉的声音带著岁月的沧桑,目光从儿子身上的官袍移向窗外停泊的船队。
沈廷扬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放下时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响,杯盖边缘的描金还很鲜亮:“父亲,新华那边刚送从占城运来了两千石糙米,足够营地支撑半个多月。”
“咱们的沙船昨日从松江回来,又拉了三百石杂粮,其中有一百五十石是红薯干,耐放得很,支撑到下月应当无虞。”
他顿了顿,又道从袖中掏出一本帐册,摊在桌上:“只是近来从江北逃过来的难民越来越多,每日新增不下百人。照此情形,不出月余,粮食消耗就要翻倍。
;
“新华的移民船该来了吧?”沈墉捻动佛珠,轻声问道。
“算算日子,也该来了。”沈廷扬抬眼望向窗外。
“来了就好。”沈墉嘆了一口气,“都是活生生的人命,能收多少,就收多少吧。
“父亲说得是。”沈廷扬頷首,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北方,“只是这大明的天..
怕是真的要变了。
“6
沈墉捻动佛珠的手微微一顿:“我们沈家在崇明立足四代,靠的就是“守业先守心“。
当年你祖父接手家业时,恰逢海禁鬆动,他顶著压力造了二十艘沙船,打通了南北海运,才有了今日的基业。”
他的眼神变得悠远,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往昔:“记得隆庆二年,你祖父率船队顶著颱风北上,將江南的丝绸运往辽东,再载回关外的毛皮。那一趟的利润,就够置办百亩良田。
66
“如今乱世將至......“沈墉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多积些阴德,也是为家族多留条后路。”
沈廷扬顺著父亲的话语补充道:“咱们现在不光有船有田,还有家丁武装,三百多个水手都是世代跟著咱家的,水里陆上都能打,上次海盗袭扰码头,不就是他们打退的?
”
他话锋一转,神色凝重:“只是眼下局势......孙传庭兵败澠池,闯贼已然称帝,听说不日就要北上京师,而各地镇军皆观望畏缩。我沈家今后的路,確实该好生思量了。”
提到后路,沈廷扬突然想到了什么,將手中的帐册合上,声音压低了些:“父亲,去新洲的族侄沈明昨天回来了,带来了不少东西,正在偏厅等著回话。”
沈墉眼睛一亮,猛地坐直身子,翡翠佛珠停在指尖:“快让他进来!”
不多时,就见一个身著锦衣蓝衫、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走进来,正是去年前往新洲大陆考察的族孙沈明。
他见到二人立刻跪倒在地,声音带著长途跋涉的沙哑,却难掩激动:“孙儿见过祖父!”
“此去新洲,可有收穫?”沈墉抬抬手,示意他起身回话。
“回祖父,新洲可谓是————是一块天赐福地啊!————孙儿这趟没白去!
“嗯?”沈墉与沈廷扬互相看了一眼,眉头皆向上挑了一下,“详细道来!”
“是,祖父。”沈明再次躬身一礼,隨即开始讲述他在新洲的所见所闻。
他说新洲大陆广袤无垠,比大明大上数倍,骑马奔驰半个月,都没看到边。
那里的树木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合抱,河里的鱼密集得能载起孩童。
还有河谷和山间肥沃的土地,种下去的玉米和小麦能堆成山。
沈明的讲述,让厅內沈氏父子二人渐渐睁大了眼睛。
新华人所建的眾多城镇,有宽的街道,都是用石板铺的,下雨天都不沾泥。
高大的砖石房屋一排一排,市井繁荣和民生富裕不亚於江南之地。
他们工厂还有自动纺纱织布的机器,一个时辰纺的纱比松江府十个织女一天纺的还多。
还有他们的冶铁厂,烟囱比沈氏沙船的枪桿还高,炼出的钢刀能砍断铜钱。
他说著,从腰下掏出一把短刀,递给沈廷扬:“伯父你看,这是新华造的,你试试锋利不?
”
沈廷扬接过短刀,刀身泛著冷光,他拿起桌上的竹筷,轻轻一砍,筷子就断成两截,面上露出讶然神情。
“新华的官员还带著我们看了他们的船厂,造的船比咱们的沙船大三五倍,船上的火炮能打十里地!”沈明兴奋地说道。
“哦,对了,他们还给了我一张新洲舆图。”说著,他又掏出一张摺叠的新洲略图,展开后铺在桌上,图上简单的標註著山川河流,“祖父你看,这就是那新洲大陆。”
“咱们要是去了,能给咱们划出几千顷土地,就是万顷也不是不可以。”
“不过,新华有授田限额,每人仅止六十亩,超过此数者,只能另行租赁经营。租金却是极为便宜,每亩地只要几角钱,租三十年,五十年都成!”
沈墉与沈廷扬对视一眼,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意动。
窗外,长江的涛声隱隱传来。
码头上,沈家的沙船正在卸货,號子声此起彼伏。
而在这间花厅里,一个关乎沈氏未来命运的决定,正在悄然酝酿。
沈墉缓缓站起身,走到窗前。
远处,江滩边难民营地的炊烟裊裊升起,与江雾融在一起。
他手中的翡翠佛珠又开始缓缓转动,每一颗珠子都在晨光中泛著温润的光泽。
“这新洲......“老人轻声自语,“或许真是条出路。
他转身时,佛珠在腕间绕了三圈:“过些日子,在各房里挑些踏实肯乾的子弟,带上几位老成的管事,再招三百农人.....
”
腕上的翡翠珠子轻轻相碰,发出玉磬般的清音,“就去那片新土,建个沈氏分支罢。
"5
沈廷扬正要开口,却见父亲从博古架上取下一只紫檀木匣。
匣盖开启,里面整齐排列著七枚翠玉印章,那是沈家在各房和各处商埠的印信。
“把松江、广州的印信取出来。“沈墉的手指抚过印章上的篆刻,“新洲分支,到时该有自家的印记了。”
>
四月十二日(1645年6月8日),长江口的风带著咸腥水气,刮过南沙镇(今崇明岛新河镇)外那片沿著江岸绵延数里的难民营地。
天刚蒙蒙亮,陈阿婆就佝僂著身子钻进芦苇盪,枯瘦的手指在泥泞里摸索,指甲缝里嵌满黑泥,半天才能扯出几根还算完整的芦苇根。
这些带著泥土的根茎,待会要在江水里反覆漂洗,才能下锅熬煮。
她的小孙子狗剩蹲在窝棚口,怀里抱著个豁了口的陶碗,碗沿还沾著昨天的粥渍,一双大眼睛直勾勾盯著不远处沈家粥棚的方向,喉咙里不时发出细碎的吞咽声。
窝棚是用芦苇杆和茅草搭的,顶上盖著几片破旧的油布。
昨夜下了场小雨,棚角还在滴水,地上铺著的乾草湿了大半,散发出浓重的霉味。
这样的棲身之所,在营地里隨处可见。
一万二千余难民挤在这片临江的滩涂上,密密麻麻的木屋歪扭著,橡子都是捡来的废木,有的乾脆用绳索捆著芦苇当墙。
更为简陋的,乾脆把茅草堆成穹顶,江风掠过时,整个棚顶都在晃动,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。
面容枯槁的难民们在晨雾中往来穿梭,有的背著破麻袋四处捡拾能烧的芦苇和浮木,有的围在营地边缘的江水边淘洗野菜,浑浊的江水里飘著几片菜叶。
一个妇人弯腰搓洗衣物时,后腰的补丁裂开个口子,露出里面乾瘦的皮肤。
偶尔有孩童的哭闹声被江涛吞没,隨即又响起妇人沙哑的哄劝。
营地西头传来一阵阵咳嗽声,一群河南来的难民正围著个老郎中,他手里捏著几根草药,摇头嘆道:“这是风寒入体,得有薑汤发汗才行。可这营地里,哪来寻的到生薑.————
”
“阿婆,今天能喝上稠点的粥吗?“狗剩的声音带著怯生生的期盼,小手上还沾著窝棚里的草屑。
阿婆將拾来的柴草拢好,拍了拍沾在衣襟上的泥点,目光落在远处粥棚前那面绣著“沈“字的蓝色旗帜上:“能,沈家老爷心善,还有新华来的先生们送粮,饿不死咱们。”
她的话音刚落,就见几个穿著青色短褂、腰系黑布带的汉子推著独轮车走来。
车軲轆碾过泥地发出“吱呀“声响,车上的木桶冒著热气裹挟著米香,瞬间点燃了人群的期待。
人群立刻骚动起来,捧著各式各样的容器围过去,有豁口的陶碗,有开裂的木盆,甚至还有大片荷叶捲起来的临时容器。
儘管,所有人早已飢肠轆轆,但没人敢插队。
维持秩序的沈府家丁腰挎短刀,眼神凶狠地扫过人群。
领头的家丁叫沈忠,是沈家船工的后代,胳膊上有常年摇櫓磨出的厚茧,见有人往前挤,立即沉喝道:“都排好队!沈老爷说了,人人有份!谁敢乱来,就取消今日份例!
66
人群霎时安静下来,只剩下木勺刮过桶底的沙沙声。
更远处的哨卡旁,几个新华武装民兵正倚在寨墙上休息,他们穿著灰色號衣(军装),手中端著火统,一脸戚戚地望著这边。
南沙镇东头的沈府,却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青瓦粉墙的宅院连绵数亩,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威风凛凛,门楣上掛著“资善堂“的匾额,那是万历年间某位致仕阁老亲赐的。
专用码头停靠著十余艘高大的沙船,船身漆成深褐色,船头雕刻的虎头在晨光中栩棚如生。
船帆卷在桅杆上,“沈氏船行“四个大字隱约可见,脚夫们正扛著粮袋往返於仓库之间,沉重的脚步声在青石板上迴荡。
花厅內,年过花甲的老太爷沈墉靠在太师椅上,椅子是酸枝木做的,扶手处雕著缠枝莲纹样,他手里捏著一串翡翠佛珠,每颗珠子都温润通透。
对面坐著的沈廷扬一身青色官袍,补子上的鷺鷥纹样显示著他国子监司业的身份。
他前几日才从淮安乘船回来,脸上还带著旅途的风尘,鬢角沾著些许江雾凝成的水珠。
一套景德镇青花茶具摆在桌上,茶烟裊裊,龙井的清香在室內瀰漫。
“廷扬,难民营中的存粮还能支撑多久?“沈墉的声音带著岁月的沧桑,目光从儿子身上的官袍移向窗外停泊的船队。
沈廷扬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放下时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响,杯盖边缘的描金还很鲜亮:“父亲,新华那边刚送从占城运来了两千石糙米,足够营地支撑半个多月。”
“咱们的沙船昨日从松江回来,又拉了三百石杂粮,其中有一百五十石是红薯干,耐放得很,支撑到下月应当无虞。”
他顿了顿,又道从袖中掏出一本帐册,摊在桌上:“只是近来从江北逃过来的难民越来越多,每日新增不下百人。照此情形,不出月余,粮食消耗就要翻倍。
;
“新华的移民船该来了吧?”沈墉捻动佛珠,轻声问道。
“算算日子,也该来了。”沈廷扬抬眼望向窗外。
“来了就好。”沈墉嘆了一口气,“都是活生生的人命,能收多少,就收多少吧。
“父亲说得是。”沈廷扬頷首,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北方,“只是这大明的天..
怕是真的要变了。
“6
沈墉捻动佛珠的手微微一顿:“我们沈家在崇明立足四代,靠的就是“守业先守心“。
当年你祖父接手家业时,恰逢海禁鬆动,他顶著压力造了二十艘沙船,打通了南北海运,才有了今日的基业。”
他的眼神变得悠远,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往昔:“记得隆庆二年,你祖父率船队顶著颱风北上,將江南的丝绸运往辽东,再载回关外的毛皮。那一趟的利润,就够置办百亩良田。
66
“如今乱世將至......“沈墉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多积些阴德,也是为家族多留条后路。”
沈廷扬顺著父亲的话语补充道:“咱们现在不光有船有田,还有家丁武装,三百多个水手都是世代跟著咱家的,水里陆上都能打,上次海盗袭扰码头,不就是他们打退的?
”
他话锋一转,神色凝重:“只是眼下局势......孙传庭兵败澠池,闯贼已然称帝,听说不日就要北上京师,而各地镇军皆观望畏缩。我沈家今后的路,確实该好生思量了。”
提到后路,沈廷扬突然想到了什么,將手中的帐册合上,声音压低了些:“父亲,去新洲的族侄沈明昨天回来了,带来了不少东西,正在偏厅等著回话。”
沈墉眼睛一亮,猛地坐直身子,翡翠佛珠停在指尖:“快让他进来!”
不多时,就见一个身著锦衣蓝衫、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走进来,正是去年前往新洲大陆考察的族孙沈明。
他见到二人立刻跪倒在地,声音带著长途跋涉的沙哑,却难掩激动:“孙儿见过祖父!”
“此去新洲,可有收穫?”沈墉抬抬手,示意他起身回话。
“回祖父,新洲可谓是————是一块天赐福地啊!————孙儿这趟没白去!
“嗯?”沈墉与沈廷扬互相看了一眼,眉头皆向上挑了一下,“详细道来!”
“是,祖父。”沈明再次躬身一礼,隨即开始讲述他在新洲的所见所闻。
他说新洲大陆广袤无垠,比大明大上数倍,骑马奔驰半个月,都没看到边。
那里的树木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合抱,河里的鱼密集得能载起孩童。
还有河谷和山间肥沃的土地,种下去的玉米和小麦能堆成山。
沈明的讲述,让厅內沈氏父子二人渐渐睁大了眼睛。
新华人所建的眾多城镇,有宽的街道,都是用石板铺的,下雨天都不沾泥。
高大的砖石房屋一排一排,市井繁荣和民生富裕不亚於江南之地。
他们工厂还有自动纺纱织布的机器,一个时辰纺的纱比松江府十个织女一天纺的还多。
还有他们的冶铁厂,烟囱比沈氏沙船的枪桿还高,炼出的钢刀能砍断铜钱。
他说著,从腰下掏出一把短刀,递给沈廷扬:“伯父你看,这是新华造的,你试试锋利不?
”
沈廷扬接过短刀,刀身泛著冷光,他拿起桌上的竹筷,轻轻一砍,筷子就断成两截,面上露出讶然神情。
“新华的官员还带著我们看了他们的船厂,造的船比咱们的沙船大三五倍,船上的火炮能打十里地!”沈明兴奋地说道。
“哦,对了,他们还给了我一张新洲舆图。”说著,他又掏出一张摺叠的新洲略图,展开后铺在桌上,图上简单的標註著山川河流,“祖父你看,这就是那新洲大陆。”
“咱们要是去了,能给咱们划出几千顷土地,就是万顷也不是不可以。”
“不过,新华有授田限额,每人仅止六十亩,超过此数者,只能另行租赁经营。租金却是极为便宜,每亩地只要几角钱,租三十年,五十年都成!”
沈墉与沈廷扬对视一眼,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意动。
窗外,长江的涛声隱隱传来。
码头上,沈家的沙船正在卸货,號子声此起彼伏。
而在这间花厅里,一个关乎沈氏未来命运的决定,正在悄然酝酿。
沈墉缓缓站起身,走到窗前。
远处,江滩边难民营地的炊烟裊裊升起,与江雾融在一起。
他手中的翡翠佛珠又开始缓缓转动,每一颗珠子都在晨光中泛著温润的光泽。
“这新洲......“老人轻声自语,“或许真是条出路。
他转身时,佛珠在腕间绕了三圈:“过些日子,在各房里挑些踏实肯乾的子弟,带上几位老成的管事,再招三百农人.....
”
腕上的翡翠珠子轻轻相碰,发出玉磬般的清音,“就去那片新土,建个沈氏分支罢。
"5
沈廷扬正要开口,却见父亲从博古架上取下一只紫檀木匣。
匣盖开启,里面整齐排列著七枚翠玉印章,那是沈家在各房和各处商埠的印信。
“把松江、广州的印信取出来。“沈墉的手指抚过印章上的篆刻,“新洲分支,到时该有自家的印记了。”
>